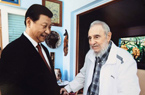新华网西宁4月4日电(记者李琳海)又是一年清明节,在高原依旧飘着雪花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海子诗歌迷来到位于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海子纪念馆,缅怀这位富有才情的早逝诗人。
记忆:“伯父海子是熟悉的陌生人”
“25年,伯父生命的长度;25年,伯父离开人世的时间;25年,一个我还没有达到的年龄。”海子的侄子查锐说。
1988年,海子来到高原,写下《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1989年3月26日,25岁的海子带着《瓦尔登湖》,躺在了山海关的铁轨上,远处隆隆火车声响起,阳光刺眼,野花怒放。
查锐,23岁,目前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在我眼中,伯父海子是熟悉的陌生人。”
査锐告诉记者,小时候对伯父的记忆,只是停留在每年春节前必须去祭奠的墓地,墓碑上刻着他和两个弟弟的名字。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总有形形色色的造访者,而他的奶奶、海子的母亲操采菊也会热心招待。
“有人提出祭奠伯父墓地时,我会成为引路者。”査锐说,那条离家约有1里地长满草的小路,他不知走了多少次。“后来我懂得,很多人带着不同的心境走过那条小路,也许他们在寻找什么,或许他们确实找到了什么。”
査锐说,25年里,海子留下的书籍还经常被他的爷爷奶奶拿出来晒晒,偶尔翻开时,他也会闻到阳光的味道和雨水的糜烂味。但在那里,他也似乎与海子产生着感情共鸣。“同样的草垛、同样的老屋、同样的南方湿漉漉的雨季,他所描绘的意向都与我幼时的记忆相差无几。”
怀念:“他用纯粹兑现着对诗歌的承诺”
山海关,长城的起点,对海子也许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25年,沧海桑田,海子的诗句,仍然历久弥新,耐人寻味。
“25年后,他成为中国诗歌文化界的重要符号,多少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还在海子留下的诗歌奇观中流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吉狄马加说。
吉狄马加说,海子的死有过多阐释,纵观25年,他已成为中国当代诗歌标志性的转折点,在短短的25年里,海子在贫苦、单调与孤独中,留下了近200万字的作品。
“他用诗歌与生命的冲击,将无法淡忘刻在了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中。”吉狄马加说,作为一名农民的儿子,这个沾有“麦地”文化的诗人在历经生活磨难后,用一种极端方式选择了离开世界,然而,在他有限的25年生命历程中,他用“纯粹”兑现着对诗歌的承诺。
查锐说,对逝者而言,他们对于世界的记忆永远留在了去世之前,他们的青春与理想都定格在了那一瞬间;对于生者,怀念却成为时间给的空气。
“在我们心里,住着一个硕大的月亮,月亮的名字,念作海子。”网友这样表达对海子的怀念。
温情:种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
25年前在山海关的一瞬间,海子带走了耀眼的光芒,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还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
“每一个读过伯父诗的人,每一个对他诗歌有独特感受的人,都会为伯父和他的诗留有一块空地,在上面种上自己的影子。”査锐说。
吉狄马加说,25年里,人们对海子的离去有过多阐释,但我坚信,他的作品是明亮的,充满温情与希望,在他的诗中,赞颂着奉献,他用理想主义追求人类的精神高地,他也让劳动充满意义。
“在他的诗中,他为别人的幸福感到幸福,他用温暖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的赞颂。”吉狄马加说。
海子的父亲査正全一生中共建过8座房子,但在2004年,他与妻子操采菊在安徽老家为海子修建的海子故居已成为他一生的荣耀。
査锐说,如今老人年事已高,他们已不再种菜,闲暇日子里,他们在海子故居追忆,读海子的诗歌。“与陌生人谈论海子,已成为家人习惯的事。”
査锐说,奶奶操采菊经常会用安庆口音朗诵海子的《以梦为马》,而在千里外的青海,在每隔两年举办的中国海子青年诗歌节上,高原人民用藏语、蒙古语、汉语,动情朗诵海子的诗作。
“25年,我相信伯父完成了该完成的,除了诗歌,已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诗歌是他留下的唯一记忆。”査锐说。
(来源:新华网)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