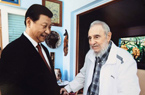资料图片


策划:赵洁
文:北京站记者 程雪超
非遗传承人
古琴 杨青
古琴:
古琴,又称琴、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琴,有文字可考已有着4千年以上历史,是汉民族最早的拨弦乐器之一,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初为5弦,后传说周文王和周武王各加一根弦,始定为7弦。琴是中国古代文化地位最崇高的乐器,位列中国传统文化四艺“琴棋书画”之首,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现存琴曲3千余首。2003年,古琴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青是其传承人之一。
在很多人眼里,古琴因其厚重的文化内涵而多少有些神秘色彩,因此,影视剧中常是帝王将相或文人名士才通晓古琴。但古琴名家杨青介绍说:实际上,古琴在古代的认知度极高,是离人们日常生活很近的乐器。如今,杨青开班授课,教授弟子,倡导以古琴接近国学,以琴声宁静内心:“就像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时弹奏《凤求凰》,伯牙找不到知音时弹《高山》、《流水》,子期听懂了——琴能表达我们想表达却不好表达的情感。”
“古琴无大师”
杨青第一次接触古琴是在1975年。当时有上海、北京、辽宁三个艺术团一起出国演出,上海团表演了古琴,当时身为琵琶演奏家的杨青第一次听到了优雅的古琴音乐。
“由于古琴的音量小,不适合彼时专业文艺演出,古琴一直深藏高阁,知道和学习的人并不多。”而在2001年成立了“中国琴会”这个学术团体后,古琴才加快走出书斋和小范围的雅集,走进各大音乐厅和艺术盛会。古琴有了全国的学术活动,甚至有比赛,有考级,有各种各样的大型演出。2003年,古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逐渐得到重视。
那次演出后,杨青开始学习古琴,从此,古琴成为他一生的事业。杨青称,古琴并非传说中那样神秘。“在技术上,古琴是弹拨乐器中最简单的了,弹拨技术很容易掌握。”而真正难倒今人的是古琴文化,即“意境”,它的书籍、曲谱太多,“古代有很多弹古琴的人会写一些美学、意象上的感悟,技术熟练以后弹曲还得能表达出意韵,通过琴曲表达内心世界与对人生、自然、琴道的感悟。所以琴学很深,深到可能你一辈子都悟不透,古琴就难在这儿。”
杨青称,古琴“难”还难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期,会制作古琴的人很少。“但一张明代老琴就得值一百多万,谁能弹得起?”而现在,随着古琴制作工艺发展,万元左右就能有张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好琴,古琴艺术逐渐恢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古琴。也有很多古琴演奏家登台演出、讲座,但杨青不赞成把古琴演奏家称为大师,“如果是明白人,都知道古琴无大师,因为古琴是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乐器,那么多流派,那么多琴谱,那么多文史的东西,谁能穷极它啊?”因此,当有人称他为古琴大师时,他特别惶恐。
“古琴救了我的手”
1986年时,杨青的人生发生了很大变故。有一次,在擦玻璃窗时右手臂不幸摔伤,断了五根肌腱,尺神经也断了,两次修复手术,右手缝了49针 ,但痛苦之下却是古琴救了他。“我把古琴坚持弹了下去,是古琴救了我的手,因为它刚好是种有机的物理疗法。”
作为一名军人,杨青1986年曾奔赴老山前线,“我们文工团军人就住在军部, 前面就是战地卫生所,官兵们的生死伤痛就发生在眼前,而最难过的莫过于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拎着一只桶走过,里面盛着的正是伤兵的一只断脚。”看过许多生死, 从前线回来后,古琴再没有离开过杨青,他会在汶川地震的映秀镇抚琴弹一曲《忆古人》追忆那些故去的人;也会在岳阳楼对面君山上的娥黄、女英二妃墓前,弹一曲《湘妃怨》,而每每当他的琴声响起,听者中常有潸然泪下的。
“与那么多学者、音乐家交流,尤其到欧美国家跟国外艺术家交流时,说再多都不如坐下来抚一曲古琴曲。”杨青如此感叹,他曾组织或参加国乐艺术团赴美国、欧洲多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地进行友好访问演出。而当他在日本奏起古琴曲《流水》时,也令日本著名传统音乐家赞叹不已,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杨青现在又开始将古琴音乐与国学经典结合在一起,正在编著《琴诵诗经》和《礼乐三十课》,而学习古琴更能帮助成年人,弹古琴会让人姿态优雅、心态宁静,适合调整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在这份沉静中体会、感悟生命的本质。
“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在异国打拼,当没有朋友、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有一张琴就不会绝望。因为弹琴时能听到浓浓的乡音,音乐是最忠实的伴侣。”
打破“儿童不能学古琴”的桎梏
杨青在古琴教育方面倾心十数年心血,更打破了儿童不能学古琴的无形桎梏。“在2000年7月18号,北京市少年宫的古琴班规定十岁以上孩子可以学,可偏偏有五岁的要报名,家长们跟我说‘我们都三四十岁,想学古琴学不到,能不能收下我们,我们和孩子一起学。”杨青力排众议收了七个五岁的孩子,而琴桌边常坐的是一家三口。孩子们很多在学了三五个月后,就超过家长的水平了。感悟音乐,孩子们更敏感。
在中科院力学所,杨青开设的古琴班上收下的多是退休的科学家,最年长的76岁。在他的学生当中,有一对东北的老夫妻,每次来京都租房三个月,专程跟杨青学习。他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小伙子,左手中指没有第一截。“他问我能学么,我说,越是这样我越要帮。”而杨青教授的一对耳朵失聪姐妹,六月份即将办专场音乐会。
杨青甚至在北京两个最好的中学——人大附中和清华附中开设了古琴班。他还将琴艺传授给了儿子。“古琴这个乐器有语言,弹琴时感觉是在和祖先对话。琴是录音机,曲谱是磁带,把对后代的寄托、教诲都融合在琴声中了。”
杨青认为古琴的传播越透明,越有利于它发展,有个别人认为杨青开班授课将古琴传给老百姓,担心把古琴变味了,他却不这么认为,“老百姓喜欢古琴,懂古琴,你想变味他还不答应。”
做一张古琴得三年工期
杨青介绍说,古琴独到之处一在低音,优雅华美、低调质朴;二在它音色沉静而兼具空灵,弹时既可以有颗粒感,又可以在弦上滑动时产生线状的优雅和缠绵。
“古琴艺术最宝贵的莫过于《流水》、《梅花三弄》等三千首古琴曲,古琴曲谱实际是中国古典音乐的宝库。“中阮是古乐器,秦代称为秦琵琶,可没有一首古代阮曲传下来;琵琶是波斯乐器,从公元初进来,有《塞上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几首古曲;而古筝做为从春秋战国时传下的乐器,几乎没有古曲传下,现今的筝曲大都是移植别的乐器曲目或现代曲。而像古琴,从唐朝以前至今,算上同名不同版本的有三千首原汁原味的古曲。”
由此,古琴也吸引了很多现代音乐人的钟爱,窦唯就曾跟青年古琴艺术家巫娜学习;而齐秦就专门从大陆背一个古琴回台湾。
古琴自古以来是比较贵的艺术品,什么才是好的古琴?杨青称,古琴音色与材质息息相关。制作古琴最好是老的桐木、杉木,木头历经百年,干燥坚硬如石,用手敲打,音色纯净清亮。做一张古琴,按传统工艺得三年工期,杨青说:“首先做好面板里面的槽腹共鸣结构,然后两个木头合在一起,最后一遍一遍地打灰胎,这灰胎是什么?用鹿角霜(就是梅花鹿的角磨成粉),然后跟大漆一遍一遍地和匀,完了在古琴的木胎上刮薄薄的一层。随后放在窨房里面,在高湿度、恒温的条件下阴干,七天以上才能表干,干了以后非常坚硬。接下来还要打磨,再刮第二遍漆胎,如此反复,一层再一层使漆胎达到一定厚度,最后还要上面漆。”按照这样传统工艺制作的古琴,使用寿命特别长,现在保留下来的唐代的琴还可以很好地演奏。
(来源:广州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