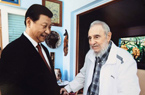▲爱因斯坦(左)与泰戈尔

▼大江健三郎(左)与小泽征尔

▲杨振宁(左一)与莫言

王蒙(左)与柳传志

在音乐家谭盾与建筑师王澍的对话中,相信您已经感受到了跨界对话擦出的火花。
其实,从泰戈尔与爱因斯坦,到大江健三郎与小泽征尔,再到杨振宁与莫言,妙趣横生的跨界碰撞从未间断,也仍将继续。
泰戈尔与爱因斯坦
就像两个来自不同星球的人在交谈
1930年,泰戈尔和爱因斯坦在德国首次会面。在那次会面中,黛米瑞·马瑞安诺夫,爱因斯坦的一位亲戚,描述泰戈尔是“具有思想家头脑的诗人”,而爱因斯坦是“具有诗人头脑的思想家”。他后来补充说:两个人的这次对话“就像两个来自不同星球的人在交谈”。
他们的会面是在爱因斯坦位于柏林外山顶上的家里。当时42岁的爱因斯坦走下山来迎接他70岁的印度客人。这位客人后来这样回忆主人:“他浓浓的白发,闪耀着光芒的双眼,温暖的态度,以及可以如此抽象地用几何和数学法则处理问题的个性特征让我印象深刻。”
泰戈尔为爱因斯坦极度的简单所深深震惊:“他身上没有任何死板的特性,也没有因为智慧而超然。在我看来,他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真的感兴趣并且能够理解。”
在很多方面,这两位伟大人物是不同的:国籍、文化背景、职业以及专注点;但他们仍然因为对方的贡献,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音乐的热爱而联系在一起。从泰戈尔和爱因斯坦的对话中,可以洞察两个人的创造力和人生观,以及对艺术的兴趣。他们的谈话涉及真理的真实性和自然性:爱因斯坦疑惑是否真理和美可以不依赖人而存在,“如果人类不再存在”,爱因斯坦假设,“贝耳维德勒的阿波罗像也将不再美丽”。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又在柏林会面了,这是他们在1930年到1931年四次会面中的第二次。他们拍了合影,两人都留着胡子——爱因斯坦是小胡子,而泰戈尔是长长的白胡须。拍照时两人双手相扣,看着照相机。
在这次对话中,两人都同意音乐的美是无法分析的。泰戈尔说:“分析东西方音乐对我是如此困难。我深深地被西方音乐所打动,其结构巨大、组成宏伟,而我们自己的音乐更深地打动我是因为它的热情表达。”
爱因斯坦回应说:“我们想知道音乐是一种习惯,还是人类的基本感觉;感受协调和不协调是自然的,还是我们所接受的习惯。”
他继续说:“对于我来讲,经历中的所有基本事物,我们对艺术的反应,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一样有不确定性。即使我面前放在桌上的红花,对你对我都是不一样的。”
泰戈尔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此观点,而是试图找到东西方的折中点。他说:“他们之间总会有协调的过程,个体的鉴赏力遵照普遍的标准。”
其实,早在会面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书信提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1929年12月22日泰戈尔在给爱因斯坦的明信片中写道的,“我向知道我不完美却仍然热爱我的人致意”。
大江健三郎与小泽征尔
充满触类旁通的惊喜和豁然开朗的愉悦
曾获诺贝尔奖的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与世界知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也曾有过文学与音乐的跨界对话。
两人同为1935年生人,同为顶级艺术家。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哈佛大学同时授予他们名誉博士学位。借此契机,有心之士为大江与小泽安排了深入畅谈的机会。
虽是同龄人;但大江和小泽成长环境很是不同。大江出生在日本四国,小泽出生在当时还被称为奉天的中国沈阳。一个是整天奔跑在树木花草中,不断冒出“为什么树总是垂直长高,横过来长不可以么”之类奇怪想法的乡下小孩;一个是被信教的母亲硬拉到教堂唱圣歌,渐渐弹起了钢琴,慢慢步入西洋音乐殿堂的早慧少年。
然而,无论是大自然的山风海语、鸟鸣树萧,还是人类的智慧结晶、伟大作品,都给予了他们美的熏陶,并将艺术的种子深深埋下。同在15岁时,大江和小泽确立了自己关于文学和音乐的梦想和目标。尽管一个被父亲说“音乐家没饭吃”,一个被老师说“像你这样的每年有上千个去东京”,他们还是沿着自己选择的路走来,披荆斩棘,走到了几十年后的辉煌。
当大江遇到小泽,尽管从事领域不同;但交谈起来却非常自然。两位大师之间有着一位特别的“联系人”——大江健三郎那位先天智障、却有惊人音乐天赋的长子光子。大江与光子通过声音交流,光子通过创作音乐与世界联系、沟通,这让大江深刻理解到,音乐的本质也是沟通与交流,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是相通的。
于是,这场音乐与文学的谈话,变得妙趣横生,充满着触类旁通的惊喜和豁然开朗的愉悦。当小泽提到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弦,说它是“音乐横向运动中的纵向表现”时,大江立刻应和说,在文学中也有类似和弦的表现:“那就是隐喻”——和弦增添了音乐的丰富感与层次感,而隐喻也能在不干扰语言叙述横向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创造意境。当小泽说到一个音乐术语“弱起”时,大江又马上心领神会:“弱起的意思是从低处向上抬高,这和诗歌不吻而合。诗的形式是第一个音节从弱音开始,渐次变强。”
思想的交汇与碰撞,为我们展示了两位大师丰富的内心世界。小泽敏锐、热忱,大江深厚、睿智。小泽是一个优秀的发现者,思维天马行空,话题从音乐教育到幽默感,再到人情味,不断游走。强烈的直觉感和活泼的生命力,令他总能处处有所发现;而大江则是一个完美的阐释者和挖掘者,所有小泽抛来的问题,都能在他这里得到适当的回应和完善、深刻的表达。他那长年文学创作与观察社会所形成的溯归本源的思考方式,为这场对谈提供了更广泛的思索空间。
杨振宁与莫言
在两位诺奖得主之间,隔着很长时间
莫言和杨振宁坐在各自的沙发上,之间只隔着一个茶几;但是在两位诺奖得主之间,却隔着很长时间。
杨振宁35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是1957年。那时候,瑞典皇后陪着诺奖得主,瑞典国王陪着诺奖得主的夫人一起步入那历史性的时刻。后来,瑞典国王有了儿子,又有了孙子,也就是现在的瑞典国王。
2012年1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厅里,现任瑞典国王为莫言颁奖。
杨振宁与莫言确实相差很远,年龄相差33岁,获奖时间相距55年,而且从未谋面。席间莫言说,今天见到了当年在他心中像神一样的杨振宁。当年他知道很多流传的关于杨振宁的“段子”,段子里的杨振宁是掌握很多钥匙的“神”。在莫言的心中,诺奖与诺奖的含金量也不一样,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是文学奖不能相比的,那些奖在他眼里才是“真金”。
莫言说,他能得奖,是因为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进步,就没有他这么个作家。杨振宁说,他回国9年多了,他觉得中国最大的改变,不是建起了很多高楼大厦,而是农村和农民的思维方式。
对话开始前,杨振宁一见莫言就坐到莫言身旁的沙发上,像小记者一样连连发问:你是怎样一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年逾90岁的人,依然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探索的精神。
在谈到文学和科学的关系时,莫言说,文学创作和科学有很多不同。文学关注人,科学关注自然界;文学家关注人类情感,科学家关注物质原理。严格地说,作家的创作也不是无中生有,很多作品都是经过现实人物想象加工的综合;但又不能和任何人对上号,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更自由的地方。杨振宁则认为,科学里更多是去发现,而文学里更多是去发明,但两者都需要“妙悟”和“想象力”。
“如果把爱迪生请来,在这个世界生活一个礼拜,哪一个东西是他最意想不到的?”当92岁的杨振宁问出这个孩子般调皮的问题时,全场爆发出笑声。很快,莫言接道:“手机,我觉得是手机。”“我也同意是手机,用这个东西,我们就能和远在美国的人通话,多神奇啊。”杨振宁说。
主持人请两位诺奖得主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心中的中国梦。杨振宁说,这不能用一两句话来讲;但我相信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中国梦会实现。莫言则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述风格:“我在网上看到有征集去火星的志愿者,中国人报名的很多,这也表达了一种梦想——到天上去。”
王蒙与柳传志
两个有着相同感受的人,终于坐在一起聊聊
2013年10月,文化部原部长、当代文坛重量级人物王蒙发表了一篇题为《科技战胜人类的噩梦》的文章,表示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电脑、手机“杀”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受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对王蒙的忧虑表示“感同身受;但也只能叹息”。他在微信上对王蒙文章的转载,再次掀起一轮人们关于科技与文化的热议。
2013年年底,王蒙和柳传志先生,分别来自文化界和企业界;但有着相同感受的人,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面对面聊聊。
柳传志在向王蒙讲述他是如何用时间改变人们对联想看法时透露,“联想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拿不到批文,就想了个办法,到香港办了一个小厂,然后将产品带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恰好赶上我国主管部门的一位处长在这个展上看到了我们的产品,感叹这儿还有一个中国企业的展位,而且还是北京人,这才给了我们批文,也算是‘曲线救国’”。
虽然两人身在不同的业界;但王蒙也有同感,他也回忆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次我到纽约开会,有些华人作家在谈到一些问题时说看不起中国作家,认为中国作家缺乏责任感。他们大声质问‘中国的作家在哪儿’,我回答他们‘中国作家当然在中国’,中国作家对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判断。”
这次聊天,话题当然离不开那篇《科技战胜人类的噩梦》。王蒙说道,其实本来中国移动互联不是问题;但中国内地缺少相对多元化的接口。
“比如香港,有一些封闭性俱乐部,一进门,就要求关上手机,如果手机响了,就会请你出去。重要的场合都是如此。而我们呢?经常能看到一些主持会议的人在上面说话,下面很多人都在看手机。这起码是不礼貌。当然,我走哪儿也用手机。一次我参加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议,我正在听讲话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我想‘什么事呢’,一看,我太太发来了短信提醒我开会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嗨,丢人丢大发了。”
柳传志接着说:“从历史长河来看,这是一个过程。中国人由穷到富,会慢慢变得更有礼貌、更有教养。这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过程,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如何让这个过程尽早结束,这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如果成天不看书,这事就麻烦了。”
(王一 综合)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