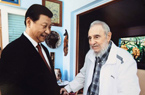金宇澄
“从网络到读者”,是“思南读书会”我讲《繁花》创作的一个题目,题头引用穆旦的诗“用语言照明世界”,这是穆旦《诗八首》里的一首,说是爱情诗,非常能反映《繁花》写作的整体感受,在无数次的摸索中,体验语言的复杂的心情,体验难以明言的一种语境。我在《繁花》的内文和跋中,分别引了这首诗,同时把这首情诗印在封四,一本小说,三次出现这首诗歌,以表我的敬意。穆旦是非常优秀的诗人,非常感谢他。
《繁花》初稿是在一个叫“弄堂网”完成的,这恰巧是个上海话背景的网站。以后有媒体记者曾问我,为什么写上海话?那实在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
2011年5月10日的中午11点,我用 “独上阁楼”网名写了一个开场白,从这天开始我每天发帖,14日那天,写到了《繁花》引子的开头,就这样,逐渐欲罢不能,每天300、400字,500、600字,甚至每天6000多字,出差到外地,赶到网吧去写,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写作状态。
网上连载的好处是,能够不间断得到读者激励。读者和作者的关系非常近,西方习惯作品朗读会,其实是过去盛行的几个朋友听作者朗读稿子,然后提意见的古老写作传统。我每天写,得到读者随之而来的阅读心得和意见,一种不断促进的积极过程,大半年时间,《繁花》初稿就出来了。
《繁花》网上连载,开头基本是上海话,和小说不一样,上海话味道非常浓。最后三分之二,我已意识到不能只让上海人读懂,从事20多年的文学编辑,方言需要转化,让更多读者看懂接受,是编辑一贯的工作目标。
《繁花》的结构,是把一种陈旧的长篇观念,所谓大树结构,改变成灌木的灵活样式,生命力同样强劲,密集的方式,相互穿插,可省去很多拖沓的叙事,一块一块延续,可互相交叠。
新旧交替两个时空,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长度是不一样的。60年代这一块,相对来说大概十几年吧,但新时代这一块,尤其汪小姐去常熟,到小说结尾怀孕,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这都是有意的,新旧交替的细部都不一样,时间长度也不一样,是一种相互的平衡对照的趣味。
《繁花》的主题和内容。我用“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做解释,这句话是过去文人的情调,一直是被主流批判的,几个文人闲聊,借此消磨时光的意趣,注意到的是闲散的、非主流的生活意趣,牵涉到和包含的内容,是生活最本质的画面,我是想收罗城市生活的细节,当然它不可能很够,但可以作为一个索引,以后的读者,看这时的上海生活,会知道上海是什么样子,上海人当时是什么样,如果不这样罗列特征,你说时代和时代还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30年代茅盾、穆时英的作品,那时代作家的处理,都非常平衡,哪怕茅盾符合阶级分析论的 《子夜》,也会写了市中心就写棚户,这才是一种公平的方法。就是说,表现上一定是一个公平的方法,不能光是写一写靡靡之音,写某种单边的内容。当然,靡靡之音写足了也好看,但写不足,因此任何方面,包括靡靡之音,《繁花》里都扯到一点,以求一种平衡。
另外我觉得,人性恶、环境恶的这一块,在上海书写、城市书写之中颇不满足世俗化的内容,如果脱离上述的角度,就会轻浮。《繁花》写底层的生活,但不麻痹其中,注意一些不高雅的事情,因为有了人性恶,环境恶对照,人的环境,也会有更温暖的回味。
《繁花》有些场景,为什么要这么去描写它?比如夜总会情况或风尘女子是怎么回事,她们怎么与社会产生交流?上次我听一位作家说,不敢写,我要是写了,我老婆会说,你肯定去过了。我说这不一定,网上就有那么多资料,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来稿中很集中,很多作品是不表现的,另一个是判断错误。比如女作者会写,那种地方,就是人间地狱。这就是说,作者已经忘记,小说是表现人生,而不是表现批判。很多伟大的作家的态度,是从不回避,更不容许误解,任何状态和职业人物,都值得书写,都可以感染读者,文学是人学,需要表现更为丰富的人情世态。
有些特别敏感的读者,会提问说,金老师,你对女人不是很友好,上海女人被表现得很俗,很粗鲁,怎样怎样。我惊讶发现的一件事是,最近的“豆瓣《繁花》”上,“小转铃”写了八千多字的评论,建议我担任上海“城隍老爷”,这是玩笑,但她表示了最喜欢《繁花》的人物,居然是汪小姐。有些读者会问,为什么对汪小姐这么残酷,让她生怪胎什么的,我没想到一个女读者最喜欢的人物是汪小姐。所以,包括我写阿宝跟李李半夜三更吃羊肉火锅,隔壁桌子有个上海的“基层女人”,和一个挂金项链的“龌龊皮鞋男人”也吃火锅,写最后他们分手,男人拍一记女人屁股,她一扭头就走了,是有意味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经常表现这种底层风景,那是因为,如果城市里有经久不衰的,贵族趣味旗袍大家闺秀,就更应该有大量不雅的,生动的普通的女人、基层女人。
《繁花》就是这样,可称为一种改良,或“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结合西方小说元素,晚清时代某种说法——“西体中用”,“牛体马用”,一生一世,逐渐低落,表现了人生的下坡路。过去有句话叫 “篇终皆混茫”,是说文章结束时候,连接到混沌和茫然,我理解为“曲终人不散”的意思,人散是结束,不散的意思,实际上也可以这么重复轮回,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传统的审美,也就是花无百日红,乐极生悲,可能是一种很老套的方式,包括我在《繁花》里提到,有个40年代的小说家无名氏,最后死得很惨,死在台湾,一个空房子里。无名氏曾经的语录是:我的时代,腐烂与死亡。
因此《繁花》在结尾不是很讨喜,鲁迅先生说过一个故事,给孩子庆生,只有一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这种结尾,说起来有些悲哀。当然在中国这么多小说里面,它只不过是其中一本。这就是我的一个关于文字方面的《繁花》解读。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