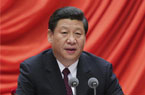性学家史成礼教授在普及性学知识


史成礼教授著作
口述 史成礼
整理 张海龙
中国当代有三大性学家——号称“北潘、南刘、西史”。北潘是北京的潘绥铭教授;南刘是上海的刘达临教授;西史,说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史成礼,他在西北兰州,素以研究性医学、计划生育和性文化著称。
说起来,史成礼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关联度最大的一件事,是他制定了中国避孕套的规格。他通过上千例实体测量,知道了中国男人的“底细”。
听史成礼聊起关于性的话题,总会不由自主地脸红耳热,可是老人家全不在意,他抖着两绺寿眉笑谈:如果没有性,就没有你,也没有我,也就没有人类。性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光谈人的上半截而不谈下半截,那是虚伪的,也是有问题的,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
说出来吓人一跳,90高龄的史成礼居然还在医院里坐堂上班,找他来看下半身毛病的人络绎不绝。
问及一生感受,他哈哈大笑着用六个字总结自己:命不好,运气好!
1
父母双亡,逃难时和舅舅失散,成了孤儿
命不好,是指我从小就成了个孤儿,又赶上闹日本鬼子,只好四处流浪乞讨——
我生于1924年,河南陕县人。我7岁时,就是日本人打进满洲那一年,我父母双亡了,只好跟着舅舅一家过活。
再往后,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人一路打进我们中原河南。1938年,蒋介石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坝,河南人就开始向外逃荒了。
兵荒马乱,我和舅舅一家人被冲散。我流落到了陕西西安,被当做“难童”收留。
当时报纸上说,日本人把中国孩子一批批送回日本及朝鲜、中国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为打仗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重返中国大陆残杀同胞。因为有这些背景,当时国民政府对流浪孩子还是很重视的,成立了各地的保育会。收留我们的,据说是张学良的叔叔,也没法考证了。
自1938年始,各地中学开始联合内迁,进驻后方各省深山古寺中,组成一批国立中学。一直到1943年,这样的国立中学共成立了22所,有十几万名学生,校名就按成立时间顺序命名。国立十中从河南迁至甘肃清水县,收留了七千多人免费学习,我被安排到那里念书。
那是乱世啊,能做到这样也相当不容易了。“文革”时我说了几句国立中学的好话,被当成了“反革命”。听说那个时候也是国民政府拿着美国援华物资做的好事,再乱也不能放松教育么。
我已经十几岁了,还能得着个念书的机会,这就是我“运气好”。我念到中学三年级时,听说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医专要招生,我就动了心。我觉得不管世道乱不乱,人都得生老病死,哪儿都能有医生一碗饭吃。问题是,报考医专需要开个家庭证明,我这么个孤儿找谁弄这个去?
那个时候鬼心眼儿多啊,找了个学篆刻的同学刻了个萝卜印章,以我哥哥的名义说:“兹有我弟弟史成礼流落西安,需要报考贵学校。”盖上萝卜章。成了!
考试结果出来了,国立西北医专我是第七名录用者。
2
钻研泌尿外科,给新兵战士测量阴茎数据
1942年,我一路向西,来到兰州,就读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
也就是那一年,为了预作时局恶化应变,蒋介石曾考虑迁都兰州。他派儿子蒋经国悄悄前往兰州考察。当时喝的还是很浑浊的黄河水,要放入白矾搅拌澄清,烧开后再喝就是甜的。洗脸水是从院子里面的水井打上来的,很清澈,但含有微量盐碱,洗脸时不太舒服。
蒋经国看到兰州四围群山干枯,认为兰州缺水是个大问题,迁都兰州的计划并不实际。再以后,蒋介石又来兰州视察,也认为水是个大问题,迁都兰州计划就搁浅了。
蒋家父子不喜欢兰州,他们是享受惯了不适应。我可是喜欢极了兰州,我这么个从小要饭的叫花子,能在兰州上大学当医生,从前哪里敢想啊!这还是我运气好的证明。再说了,1942年的兰州,和你们现在想象的根本不一样,那是未沦陷的大后方,是苏联援助中国物资装备的重要中转站,连接着西北国际交通线。各路精英人马都出没在兰州,城里每天都热闹喧腾。对,就是那种生龙活虎的感觉,兰州那时就是个移民城市了。
医专学制五年,实习半年,学习非常艰苦。
194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国立兰州中央医院外科工作。我上学时有个老师叫张华麟,他当时在兰州中央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并兼任西北医专副教授。张老师对我很好,我因为穷,哪儿也不能去,只好天天看书学习,天天守在病房里,这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对性学和泌尿外科很有研究,也把我带到了这条学术道路上。
1948年,西北医专更名为兰州大学医学院,张华麟老师提拔我当了主任,然后他被送去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专修泌尿外科。两年后,他学成回国,国立兰州中央医院已经更名为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
1949年8月,兰州先解放了。连年战争,兵源缺乏,解放军四处征兵,准备继续南下。兰州各中学都有学生参军,社会上参军的也是什么人都有,我所在的兰大医学院,就负责检查这些青年从军者的健康。我当时受张华麟教授影响,已经在钻研泌尿外科了,对包茎这类男性生殖器官常见疾病有些初步认识,但还缺乏大量的调研数据来作支撑。于是,我主动提出要给这些新兵们做一下实体阴茎测量分析。我和那些小伙子们说,这个测量很重要啊,关系到你以后能不能结婚。比如说,阴茎太小了不行,包皮过长也不行,提前发现就能及时治疗。那些年轻人一听,就很高兴很坦然地接受了我的测量。
3
调查数据,成为避孕套生产厂家制定尺寸、划分型号的依据
我当时一共做了1416名成人男性阴茎实体测量分析。结果表明,常态时阴茎最长为14.5厘米,最短4厘米,平均8.375厘米;周长最大12厘米,最小4.5厘米,平均为8.3厘米;勃起时最长16厘米,最短9厘米,平均12厘米;勃起时周长最大14厘米,最小8厘米,平均10.75厘米。
那个时候,能得到这样一组数据是非常难得的,中国从来没有人搞过这类研究。1950年,我在中华医学会开会时宣读了我的这篇报告,一下子引起轰动。
哦,你的问题我听明白了,我光是在兰州一个地方做的千人测量能代表全中国的男人数据吗?我前面不是说了么,当时的兰州哪里人都有,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从数据采集广度上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1954年,我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了论文。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里是不得了的成就,也是中国性学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正因为这个成果,1956年,我被破格升为副教授,全校通过。当年全兰州只有三个副教授名额,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大医学院各一个。
1958年,青岛乳胶厂开始生产避孕套,因为没有合适的数据,只能沿用美国避孕套的规格。众所周知,因为人种原因,白种人阴茎平均值要大于黄种人,所以生产出来的避孕套总会发生“脱套”现象,从而不能实现避孕效果。
我的论文很快引起了避孕套厂家的注意。青岛乳胶厂辗转请我过去,让我帮其确定适合中国人的避孕套规格。我根据实测数据制订了大、中、小号三种标准规格,还特别设计了特号规格。当时厂家千恩万谢,我等于是解决了一个生死问题。他们请我到青岛,管吃管住,还带我去海上吃海鲜,临走给了几百块钱作为报酬,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上海乳胶厂、广州乳胶厂都请我过去指导工作,1965年始,这组调查数据正式成为当时国内避孕套生产厂家划分型号的依据。
4
因研究这个做得说不得的事,他们骂我是个“■教授”
你问我研究性学有没有什么风险?
哈哈,肯定有啊。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里,你研究性这个做得说不得的东西,又实测了那么多男人阴茎的数据,谁还会用正常眼光看你?很多人在背后骂我是个“■教授”,“■”是西北方言,就是男人生殖器,也有骂人的意思。我听到后就笑了,说得也没错,我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的,也要像这个东西一样能伸能缩。
1957年,我刚评上副教授第二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我立刻就成了批判对象。第一个揪住不放的,就是怀疑我的成分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看起来很有道理——贫农能上大学么?贫农能当教授么?一定是假的!一定是骗子!好家伙,全医学院就斗我一个人,好几千人围攻我一个!我不怕,老子当贫农当得理直气壮,从小就破衣烂衫乞讨要饭,我还能连贫农都不算了?
当时罚我扫三个厕所,两男一女,扫就扫呗,又不是多大个事!有半年多时间,一直没限制我自由,也没让我进牛棚。那时我心态很好,白天扫厕所,晚上就去打麻将。悄悄出门,找一个朋友去玩,他在隍庙对面开了个私人诊所,那段时间倒给我把麻将教会了。
医学院派出工作组去河南陕县我老家调查。家乡人还当我早死了,这下还意外知道我现在混得不错。乡亲们和工作组说起我们从前逃难的事,说起我从小父母双亡的事,说起我的悲惨身世,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那时候不就比谁苦么?工作组一回来,我立马就平反了,立即火线入党——还有啥说的么,贫农就是阶级弟兄,必须进步。
你看,我就是运气好。反右被批判还能坏事变好事,思想还没有准备好,一下就被发展成党员了。
5
很多人以为研究性学的人肯定是流氓
1959年“反右倾”,我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我研究的性学根本就不正经,又提出我是个反动“■教授”。这一路搞到北京大学吴阶平先生那里,吴先生非常生气,说:“史成礼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跟我学的泌尿外科,怎么可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呢?”吴老先生是一代医学大师,也是中国现代泌尿外科奠基人,我曾在他门下进修。他的话分量太重了。就这么着,我又躲过了一次劫难。
福祸相倚,这句话总在我身上应验。被批斗被打倒当然是坏事,可是也引来了高层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吴阶平先生帮我化解了“反动学术权威”之后,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也过问了我的事情。了解过我的整个情况之后,他说:“出身好,水平高,这样的人应当重用嘛。”
书记都这么说了,1959年,我被提拔为兰州医学院副院长。
再往下说,就到“文革”了。我当然不可能顺利过关,这下开始有人揪我的“男女关系”问题了。在很多人想象中,研究性学的人肯定是个流氓,于是就随时注意收集你的证据。
那个时候,恰好有原来的同事调回山西老家工作,留下一个13岁的女儿在上护士学校,托付给我照顾。这下可不得了,马上有人告发,说是我和这个小姑娘乱搞。这种作风问题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要判刑、要出人命的,何况人家小姑娘还那么小,我一点也不敢大意。逼到最后,怎么说人家都不相信,我只好拿出医生的“武器”——让小姑娘去接受妇科检查,一看处女膜是完整的,所有诬告也就不攻自破了。可是,这件事对那个姑娘一定有很大伤害,不知当年告发我的人现在能不能反省。
在中国,把人搞臭的方法,男女之外,就是金钱。1969年,我调去甘肃省计生委当副主任。一年省上给1800万元计生经费,给全省各地分配。这下又有了批斗的由头,有人怀疑我在这里搞贪污。既然告了,就要查实。花了好长时间,在全省各地区查账都没有问题。
后来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世泰同志找我谈话,评价我是个好干部,虽然总被人诬告,可是一没有男女关系,二没有贪污问题,让我继续努力做好工作。
6
人要活得真实一些,有欲望就是有欲望
我这辈子总共结过两次婚,情感生活很简单。
因为研究人的下半截,别人都认为我有很多男女关系。其实,我一般和女的不打交道。我年轻的时候很穷,穿得总是破破烂烂的,一心扑在工作学习上,也没机会认识女的。妻子是我的一个实习大夫,她觉得我这人很正直。1949年,我25岁时,我们就结婚了。
第一任太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工作上也很能干。她后来做到了兰州医院妇产科主任,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中,被别人联合起来给冤枉了,她实在想不通,就跳黄河自杀了。那一年,是“文革”刚开始不久吧,人和人的关系都变坏了。
我二婚是哪一年?一下想不起了。反正今年是结婚40年了,倒推一下,就是1973年。第二任太太小我十几岁,我到80多岁的时候还能做爱,我们很享受这件事。
人有了美满的性生活才能红光满面生活来劲。大画家毕加索90多岁了还能做爱,然后大清早还要打电话向朋友炫耀:我今天早上做了一把,你行么?毕加索有句话说得好:年龄迫使我们不再抽烟,可是烟瘾还是有的;做爱也是如此,虽然不做了,可是欲望还是有的。人要活得真实一些,有欲望就是有欲望,不要不承认心里的想法。
你们都叫我性学家。性学是什么?你们看,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性由心生”,所以性学就是人学,就是心理学,就是人性学。以前有人说性学就是流氓学,认为我的工作不正经。我回答他,没有性就没有你,那你是不是流氓的产物?那你是不是就不正经?
人的上半截是修养和身份,人的下半截是本色和素质。这话说得没错,我这辈子都和人的下半截打交道,所以我见到了太多人的另一面。很多人,来找我看病,来找我咨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有些人还身居高位。可是,他们的上半截和下半截根本就是错位的,活得一点儿都不真实。
当我发现下半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心病”和“文化病”时,我就被带到“性学家”这条路上来了。
7
清代大才子李渔,曾经带着姬妾们在杭州西湖边开办性讲座
性知识的普及有多重要?我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我刚做计生工作时就碰到过两件真事:一是避孕套免费派发,发下去后发现有人领了,可他妻子不久还是怀孕了。一问,他说看到计生干部把避孕套戴在手指上示意,他就以为是套在手指上;二是在农村派发时只发不解释,结果农民领回去后,不知道用法。就知道上面的人说这个东西可以不怀孕,以为是像药那样要吃下去的。于是就把避孕套切成细丝,当菜一样炒来吃了,结果当然还是怀孕了。
还有一次,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找我看病,说是结婚几年了一直怀不上孩子,两个人都是大学教师,一个教化学,一个教物理,以为躺在床上元素们就会自然跑出来发生化学反应,孕育新的生命,结婚几年了都没有真正的性生活。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性几乎随处可得,发廊桑拿方便得很。可是我们嘴上说的却不是这样,我们不承认眼前看到的东西,我们还是不拿性当回事,也就是不拿自己当回事。
1994年,我买了一套与性有关的大书,一次就花了7500元。
当时已开始房改,有人说:天哪,都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可是,这书全世界只印发500部,你说我买这部书到底值不值?这就是荷兰人高罗佩的足本《秘戏图考——明代春宫图,附论汉代到清代中国的性生活》。
它的史料价值太强了!看到那些春宫图,你就知道性作为一种隐秘的人类欢乐绝不会被压制,总要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性文化的研究成果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让人很不服气。其实,不是我们没有研究能力,而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清代大才子李渔,曾经带着姬妾们在杭州西湖边开办过性讲座,却被当时的人们骂得狗血喷头,以为他败坏了社会风气。可是,李渔的态度多么坦荡开放啊。
敦煌莫高窟有不少与“性”有关的壁画。古代父母在女儿出嫁时,都会为其准备春宫图,教她们一些基本的性爱常识,可见古人并不忌讳谈性。我们的祖先其实对性很坦然,这才是对生命应有的赞美。
相反,如今很多年轻人直到结婚前夕,家长都从未和他们谈过性。很多人仍将性和爱分割开来,认为爱是高尚的,而性是肮脏的。这样就让我们陷于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境地。美国有本著名的写性治疗的书,叫《圣床》,现在还是禁书。最早翻译过来的那次,序言是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我写的是:性不是洪水猛兽。
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
(来源:羊城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