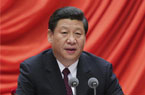《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类别:自传
新书看点
这是一位80岁高龄的传奇女子许燕吉的人生自传,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讲述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许燕吉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女儿。1941年父亲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许燕吉只有8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她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解放初,她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竟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直到1979年平反回到南京。
外祖父周大烈公是湘潭人
我祖父许南英公,台南人,曾投笔从戎,当了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日本占领台湾后,他举家逃回大陆,失了根基,穷困潦倒,客死南洋。我父亲是基督教供他上的燕京大学,所以父亲信洋教,但决不迷信。我已经有了一个前房姐姐棥新,都14岁了,比我早生20个月的哥哥苓仲,不姓许,而是随我外祖父姓周。
我外祖父周大烈公,湘潭人,是位维新派的老学究,教过书,当过官,还出过国,但他仍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连生七女竟无一男。这成了他的心病。他姑姑将贴身丫头当礼物送给他为妾,想不到还是一无所“出”。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凡娶他女儿的,必须承诺长子姓周。外祖父的愿望在五女儿和六女儿(我母亲)身上实现了。我五姨住上海,周大孙子他看不到,而我父亲和我母亲婚后就搬来与我外祖父同住,所以我哥哥虽然是“仲”,却更使外祖父欣慰,特地请了一位袁妈专门管我哥哥,染的红鸡蛋多得吃了一个月。相比之下,我的出生就雅静多了,从医院抱回来就放在厕所间里,由做粗活儿的刘妈兼照顾着。我妈妈懂科学,实行母乳喂养,我吃饱就睡,从不大哭大喊,不烦人。
外祖父给我起名燕吉。燕者,生于北京也;吉者,可冲晦气也。
再后来,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全家大小,连全部家当,又乘车又乘船,辗转数千里由北京到了香港。
1942年底逃难到衡阳上小学五年级
车到桂林停了,妈妈已经下车去了。不一会儿,领来了在桂林工作的五姑爹。他是来送我们一起回衡阳江东岸的郊区五马归槽的。下午到了衡阳市,之后到了五娘家。总算到了目的地,已是1942年底,转眼我就要满10岁了。
妈妈不久带了哥哥去衡山,还去了一趟当时南迁的省会耒阳。原来省教育厅的厅长朱经农是五姑爹的堂兄,中教科科长余先励夫妇是妈妈北师大的同学。他们都留妈妈到教育厅工作。妈妈考虑耒阳离衡阳近些,又有亲戚朋友照应,就辞了广西的聘请,春节后带了哥哥和悫哥(五娘的儿子)去耒阳,留下我在五马归槽。
五马归槽对我这城市的孩子说真是新奇世界,广阔天地。
我已经一年多没上学了,大人们给办好了手续,下一个周一,我就跟着倜哥上学了。走过田埂,走上沙石公路,约二里,路边一个大铁拱架子,牌子上面写着“粤汉铁路衡阳扶轮小学桐家垅分校”。进去是条小土路,走约50米就是个陡坡,这才看见学校原来在两座土山的狭窄山沟底下。整个学校建成三台,上面是四、五年级,中间是低年级、老师办公室和宿舍,下面是个土坪,是学生集合的操场。土坪台下是个水塘,是这条山沟的最低点。
学校在周一早上都要集会,纪念孙中山,叫“纪念周”。我们集合在土坪上,先唱升旗歌,立正,升旗。再向后转,面对上面教室外的宽房廊,那里挂着总理遗像。先唱国歌,再三鞠躬,之后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还要默哀三分钟。之后,老师讲话。
老师上课讲的是湖南话,这我都懂,因为婆婆一直讲的湖南话。同学们多半是铁路员工子弟,各省人都有,讲的是普通话。所以,一上午的工夫,我就融入了这个班级集体。我在香港只会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到这里可谓大开耳音,同学们唱的抗日歌曲我听都没听过。
妈妈到永兴三中当校长得罪了县长
转眼到了暑假,妈妈的工作忽然有了变动,由教育厅派到永兴县的省立第三中学当校长去了,我们四个都跟着走了。
坐一段火车,再坐一段木炭汽车,就到了永兴县城。永兴县城只一条石板街,省立三中在街东头,附属小学就在三中东边,操场相通,附小也走三中大门出入。
住校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打铃起床,把被子叠成方块,拿上脸盆去厨房舀水,一边洗漱,一边看大师傅造饭。湖南人一天三顿都吃干米饭,把煮得七八成熟的米用大笊篱捞到木饭甑里,剩下白稠稠的米汤舀到桶里提去喂猪,换上清水蒸甑子里的饭。早饭后,走读的同学们都来了,升旗早操,上课下课,直到降旗放学都和扶轮小学一样。
不久,生活又有了变动。这次,是飞机惹出来的祸。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我跟刘娘在中学教师食堂吃晚饭。轰隆一响,地都震动了。听到中学生们在喊:“飞机掉在河滩了!”“拿上脸盆救火!”只见河中间的沙滩上,两架飞机在熊熊燃烧。三中的学生们个个奋勇救火。后来才知道是昨夜县长在火场瞎指挥,拿文明棍打了三中的老师。学生们上去夺了县长的文明棍,七嘴八舌地训斥了县长。县长第二天上午就到学校来,让查出昨夜夺他棍子训斥他的学生,予以处分。妈妈和刘娘拒绝了,反而表扬了救火的师生。县长愤然走了,扬言学校包庇“不良分子”(共产党),决不甘休。
转眼,学期就结束了,妈妈和刘娘都被撤职。其实还是教育厅长、国民党元老朱经农力保,才没有把妈妈和刘娘当共产党“查办”。春节后,妈妈带了我和哥哥又回到衡阳五娘家,暂时失业在家。
离开仅一学期,我又回到了扶轮小学。没持续多久,长沙就被围了,不要说毕业会考,整个学校都要提前放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毛边纸油印的毕业证书。我们回到家,也看见长辈们都在忙着收拾行李。
从衡阳站上了火车,坐车的人虽然很多,但还有秩序,有座位。走了半天到达桂林。(寒影/辑)
(来源:长沙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