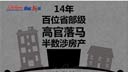□杨加深
“三希”是古人自勉之语,它既可以被理解为思想境界的升华,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一方面知识或技能的提升。
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不但是一位政治上大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一位精通汉文化的少数民族帝王。他博学多识,能诗词,擅书法,而且在对中国历代书法的收藏、保护与普及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著名的三希堂,原名“温室”,本是乾隆的书房,在故宫养心殿西暖阁。乾隆十一年(1746),因“温室”收藏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遂更名“三希堂”,匾额也是乾隆御笔。乾隆十二年(1747),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精选内府所藏历代书作,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镌刻《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此丛刻之得名,也是源自三希堂。该帖收录自魏晋至明末计134位书法家的300余件作品;乾隆十七年,又从宫内藏品中再次精选出历代名人法书五卷,摹刻上石,《三希堂法帖》终成完璧。
对“三希堂”的含义,一般人往往仅从其中收藏了三件稀世珍宝的角度去理解。古文“希”通“稀”字,何况《伯远帖》卷前引首的乾隆御题中,确实有“希世之珍”字样。录如下: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
这种“三稀”理解说,有根有据,当然可以。但如果仅仅从上述角度理解,就着实低估了这位学识渊博的“乾隆爷”了。其实三希堂之命名,还有另一个更早的来头。那就是北宋周敦颐《通书》中提出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修养论,后人简称为“三希真修”。这才是“三希堂”命名的真正源头。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三希”是古人自勉之语,它既可以被理解为思想境界的升华,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一方面知识或技能的提升。在古人的书画等级概念中,也有类似的诸如“逸”、“神”、“妙”、“能”、“精”等不同的品级差别。当然,最高境界只是一种追求而已,不一定能真正实现,拿冯友兰先生的话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达不到不要紧,但我们一直在努力!
以上只是从字面意思上讲了“三希堂”命名的两重含义。其实,即使从“三稀”的角度理解,也仍有问题。或者干脆说是乾隆皇帝看走了眼;或者为乾隆开脱一下,乾隆之前的收藏家们早就看走了眼。
何以见得?因为根据当前学者的研究,这“三稀”中,至少有一件已经被明确认定为赝品,那就是《中秋帖》。该帖之真赝,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无论其所用之竹纸,还是柔毫无心笔(从墨迹推测),均为晋代所无。明人张丑的《清河书画舫》中,就怀疑它是唐人临本,其中云:“献之《中秋帖》卷,藏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清人吴升《大观录》中则怀疑是宋人临仿,吴氏说:“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宋卷》中,进而将吴升怀疑的那个“宋人”定位到米芾身上。他说:清宫“三希”之一的王献之《中秋帖》,其实就是米芾节临《十二月帖》之本。如将二帖比勘,便能看出米氏不仅因节临而移行,打乱了原来的章法,而且“中秋”的“秋”字,把王献之的草书写法改成行书。另外,原帖三行末“如何”二字紧缩而局促,形同一字,应是不甚美观。
好在米芾也是大家,否则,乾隆爷脸上可就真挂不住了。不知道他当时是否读过《清河书画舫》,人家张丑早就怀疑了。当然,即使读过了也可以不信,但至少在命名“三希堂”时,会考虑得更严谨一点儿吧。
再说另一件。《快雪时晴帖》之真伪也争议很大,穆棣先生将这些争议归纳为真迹、唐摹善本、唐摹、北宋以前旧摹等四种说法。其中,“唐摹本说”最为鉴定界所接受。好在唐摹本也是摹本,毕竟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风。
这样,“三稀”就只剩下“二稀”或者“一稀”了,《伯远帖》遂成为唯一可以被确认的真迹,“物以稀为贵”啊!辛亥革命后,《伯远帖》和《中秋帖》流出宫外。1951年11月5日,在周总理指示下,二帖辗转数年后被重金收回,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快雪时晴贴》,1924年差点被溥仪带出宫,幸被查出扣留,后来此帖随故宫大批文物几经转徙,最终被运往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幸好那里也有一处“三希堂”。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来源:齐鲁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