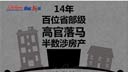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携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现身广州
美国政府部门因为经济问题部分停摆,引发人们对下半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关注。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恰在此时推出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分享了他对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未来改革的判断与研究。
中国经济和历史的下一步是回到千年的往复之中,还是走出循环进入另一番天地?吴晓波通过对中国两千年经济变革的研究表示,“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规律,从而解答现代疑问。”
文/记者 吴波
图/Gettyimages提供
为改革寻找历史规律
随着中国2013年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公布,“中国经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7.6%的增长速度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的疲软,而股市暴跌、经济增长不均衡、贫富悬殊等一系列问题,都仿佛在验证着IMF不久前的警告: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已刻不容缓!今天,人们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处发问:中国的经济将走向何方?是继续崛起,还是即将崩溃?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得出结论: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所以,需要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 ——这是吴晓波创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起点,也是最终目的。在本书中,他以时间为轴,在东西方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并且“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更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
此外,吴晓波介绍,他在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那些财政专家们对历史的影响:管仲带来了管制宏观的“凯恩斯主义”试验,他所带来的成功和副作用与世界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是一致的。商鞅则带来了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这两重遗产,并在短时期内使得秦国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最终摧毁了社会本身。王莽则是一个掉书袋的理想主义者。
王安石的变法凸现了在集权制社会中进行改革的困境:他的改革措施从逻辑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一落实到执行层面上就必然变味。然而,更令人感到扼腕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从此人们不再尝试经济上的改革,而是以稳定作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于是,就有了明清时期的僵化和保守,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也最终让给了西方文明。
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吴晓波提供了基础性的判断:国有企业、土地与金融业这三部分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谨慎的、可分步骤的,并且是可以期待的。同时,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因互联网、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等的崛起而脱离历史的藩篱,走向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未来。
对话吴晓波:
中国经济20年内超越美国
广州日报:您说在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时“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敬畏,只求寸进”,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吴晓波:创作一本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始于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的图书,很像是一次疲倦的长途旅行,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次智力与体力的考验。在闭门创作之时,我总有一种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也体会到了钱穆先生曾说过的“对古人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心境。
广州日报:为什么您说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崛起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
吴晓波:在历史上,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崛起,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广州日报:研究历代经济变革能为目前处于“后金融危机”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什么启示?
吴晓波:中国的商业界和政策的联系太紧密了,我们常讲“政商关系”,从研究历代经济变革得出的经济规律中,可以了解到,民间的繁荣与否、工商业的崛起或衰落,都在于国家政策的松紧。对于民营小企业来说,自身的抗打击力太弱,国家政策稍有异动,它的商业环境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民营小企业需要特别关注国家政策的动态,才能抓住发展机遇,做大做强。
(来源:广州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