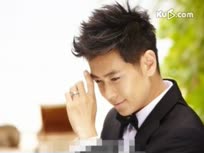已有足够的史料证明,晚清名妓赛金花使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神魂颠倒,从而“拯救民族危难于床上”的故事其实纯系杜撰。既然原本子虚,《孽海花》为何郑重其事,以无作有,并以此一纸风行,播腾众口?背后隐藏的男权文化的那点猫腻一旦说开,自然会大煞风景。
在传统中国乃至目下,普通社会里女性的“美德”,诸如温柔善良、忍辱负重、低眉顺眼、勤劳贤惠等等,都是由男人规定的,我把这称之为男权文化的女性想象;对于特殊女性人群,比如妓女,男权文化也能于“万恶淫为首”之外蹊径别开,于是有了才妓、义妓、侠妓等话头。女人真是个好东西啊,青春美体可供释放荷尔蒙;琴棋书画可供清玩风雅;于危难之际还能挺“身”而出,为国捐“躯”;妓女的侠义又供给了男人作诗的好材料,好于微醺之际就着清风明月牙疼一般地哼哼个不停,岂不快哉!
“胜利果实”的取得自然要付出成本,但若套用时下某名教授的理论,以妓女作为牺牲,当然比以良家女子作为牺牲,“危害性”要小,你们本来不就是干这个的嘛!抗战时期,女作家丁玲写了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女主人公贞贞在遭了日寇轮奸之后,竟主动走入日本军营,供日军发泄兽欲。小说写到后半方真相大白:贞贞后来主动走入日本军营,竟是受派遣以“身体”获取日军情报。贞贞既遭轮奸,已然不贞,以“不贞”之贞贞作为牺牲换取情报,付出的成本或者说“危害性”自然更小。1953年,《我在霞村的时候》成了丁玲的一个重要罪证。女作家还是太天真啊,她不懂得,有的事情说得做不得,有的事情呢,则做得说不得。
有一种说法叫“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与女性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女性(或曰母性)意味着生命的养育与保全;战争则是赤裸裸的对生命的屠杀与毁灭。然而当我们如此理解战争与女性的关系的时候,显然没有把某些特殊女性包括在内,因为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不仅不必“走开”,战争反给她们提供了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契机,使她们在精神上有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在曾朴写《孽海花》后108年,丁玲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后70年,中国名导演张艺谋拍成电影《金陵十三钗》。《金陵十三钗》所迎合的社会心理其实不是什么“商女亦知亡国恨”的英雄主义,而是以下两点:一、妓女有她们的身份原罪,这种身份原罪需要她们主动走向苦难去进行偿赎;二、说白了,让妓女去供日寇凌虐比让“纯洁”的女学生去供日寇凌虐,让我们更能平静以对。在她们挺“身”而出之前,她们的生命已然被排了座次。此处不妨再次套用某教授的理论——只是这次它的“危害性”何止是“小”,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感谢某名教授的关于“危害性”言论启发了我以上的胡思乱想。我没有法学的专业背景,所以只能利用我的文学的专业特长来一番专业灌水。现在专业灌水完毕,文章本可结束,怎奈尚有几点补充,私意至为要紧,不吐不快!
其一,“强奸陪酒女危害性小”及它的更正版“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性大”,当然有广泛的民意或者说社会心理基础。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生态里,这样的言论本该由普通社会的“愚夫愚妇”口没遮拦,实话实说,然后由某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法学专业素养对这种狭隘的“民意”指陈纠偏,从而引领社会的公共舆论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而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由名教授道出,然后众网友吐槽。这种“倒挂”现象在当前的舆论生态里已是一再发生,岂非咄咄怪事!
其二,“强奸陪酒女危害性小”引入的是受害人的“身份”这一视角;“身份”视角既可应用于受害方,也就可应用于施害方。强奸不同“身份”的人“危害性”不同,被不同“身份”的人强奸“危害性”自然也不同。比如,被富家公子强奸势必比被小偷强奸“危害性”要小;被“富二代”强奸,势必比被民工强奸危害性要小;现在是没有皇帝了,若有,被皇帝强奸,所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岂不要感激得“山呼万岁”?不是我故发杞忧,我的这番逻辑演绎某教授虽未明言,却已然呼之欲出。
其三,也许是觉得“妓女”这个词太过刺耳,某教授用了相对柔和的“陪酒女”的概念。姑不论不管是妓女还是陪酒女,她们的法律身份都是公民,其实说到底,我们并无多少理由和资格歧视妓女,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学习做人——尤其是做个好人的第一步。
(来源:羊城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