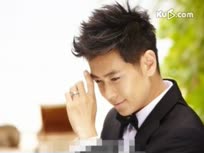湖北日报讯 一提到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女士的名字,许多读者可能耳熟能详,但是,说到她的父亲周苍柏先生,我们也许就比较陌生了。周苍柏(1888—1970)是中国现代著名银行家、金融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周苍柏一家早年在武汉生活过一段时期,他的故居,位于今天的汉口黎黄陂路上,名为“黄陂村”5号和6号的两个小院落。当地老居民称为“周公馆”。不过,要寻访周苍柏故居,我们得先从周家的私家园林“海光农圃”说起。
我在武汉东湖边居住了二十多年,几乎每天黄昏时分,都会去湖畔散散步、看看湖水。要说东湖最美的地方,在我看来,既不在游人熙攘的长天楼、行吟阁附近,也不在磨山脚下那片仿古的“楚城”周边,而是在古木森森、芳草萋萋的“海光农圃”一带。而“海光农圃”的最佳去处,又在幽静的“苍柏园”里。
“苍柏园”,是为纪念武汉东湖景区和“海光农圃”的创建者周苍柏而兴建的一处小园林。这里原本就是“海光农圃”的一部分。沿着湖边一条两旁长着高大的悬铃木的林阴道往南,可见“海光农圃”的高大牌坊。“海光农圃”四个字,系周苍柏的父亲周韵宣先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所书。走到尽头,就是“苍柏园”的小牌坊。进了小牌坊,拾级而上,可见几株足有环抱之粗的香樟树,古树的幽香会引导着你踏入一块平坦的芳草地,芳草地中央矗立着一座三人青铜塑像,那是周苍柏先生和他的长女周小燕,还有他的儿子周德佑,一位在中学念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十八岁时就在抗日宣传前线不幸染病夭折的小提琴手。
这座塑像,是根据周苍柏1937年携儿子、女儿在东湖畔拍下的一帧照片创作的。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和最令人感动的塑像之一。亲情怡怡的两代人,却在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毅然舍弃家园,共赴了国难。当时,周苍柏几乎倾尽全部家产,甚至捐出了准备送儿子去欧洲留学的钱资,援助了正在汉口领导着全民抗日救国事业的共产党人,并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结下了深笃的友情。1949年10月,周先生去北平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一回到武汉,他就把位于东湖西北岸边的、周氏家族培植和修整了数十年的私家园林“海光农圃”,捐赠给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更名为“东湖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东湖风景区前身,周先生因此也被后来人尊称为“东湖之父”。这座塑像,可以说是凝聚着两代人的家国之梦。两代人用共同的赤子情怀,谱写了一曲气冲霄汉、响遏流云的爱国乐章。
与塑像毗邻的,是周苍柏母亲的一块小墓地。这是周先生当年亲自为慈母选定的墓地。他亲手栽植的七棵丹桂,环绕着母亲朴素的墓地。如今,这七棵桂树已近九十年树龄,一到秋天,桂花盛开,散发着浓郁的芬芳,仿佛是慈母默默的心香,日夜伴随在后辈们身旁。
墓地右侧有几丛翠绿的慈竹,掩映着一个小院门。进入院门,顿觉豁然开朗:两座古色古香的、有着雕梁飞檐和朱墙碧瓦的古典式屋宇,坐落在幽静和雅致的小院里。院子里栽种着高大的桂树和玉兰树,清澈的小潭里摇动着几株红荷,小小的、曲折的廊桥,连通着两座安静的屋宇。这里就是“周苍柏纪念馆”,馆里收藏着周先生当年穿过的大衣、弹过的钢琴、读过的书籍等。虽然陈设简单,却显得特别肃静、温馨和雅致。六七十年前的老器物,都在默默地见证和诉说着周先生和他的家人从前的故事……
周先生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其祖上由江西乐平迁至湖北武昌,先是在武昌大堤口开设“周天顺炉房”,后来搬到汉阳双街弹夹巷,改“周天顺”为“周恒顺”,经营机器制造业。这是武汉机器制造业的鼻祖。到周先生的父亲周韵宣这一代时,周家已由工业而又涉足商界。周韵宣在汉口龙王庙开设了“鼎孚行”,成为了当时遐迩闻名的实业家和资本家。
殷实的家境,使周苍柏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是武昌昙华林文华书院早期学子之一。在这所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高等学府里,他接受了人文主义和神学的启蒙。民国初年,他从文华书院转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今天的上海交大前身)。这是他由文科而迈向理工和商科的一个转折点。南洋公学读完之后,他远赴美国留学,在纽约大学攻读银行专业。1917年学成归国回到上海,正式进入了金融界,先是担任上海商业银行总行会计,不久就回到了故乡汉口,担任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副行长。1926年开始任汉口分行行长。
周先生是在1919年回到汉口的,这时候他的长女小燕已满两周岁。他在汉口黎黄陂路置备了两座院落,作为全家人居住的公馆。黎黄陂路上有许多百年老房子,靠近“美国海军青年会”那栋法式老建筑,有一条僻静的小巷,一拐进短短的小巷,你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三个古老的小院落一字排开,每个小院落里都连着一座漂亮的小洋楼。这里的门牌为“黄陂村5号”和“黄陂村6号”,其中“黄陂村6号”有两个院落。当地老居民都知道,这三栋小楼都属于“周公馆”。小楼都是一色的青砖墙面、方尖形四脊瓦顶,阁楼上开着俗称的“老虎窗”,还有宽大的拱券门通往露台,露台上搭盖着红瓦顶。院子里有香樟树和梧桐树,使古旧的小楼显得十分优雅和幽静。
当年,周苍柏先生白天去离此不远的江汉路上、他所供职的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大楼上班,晚上就回到公馆里,和夫人董燕梁及孩子们待在一起,一家人亲情怡怡、其乐融融。周家的外地亲友来汉口,一般也在“周公馆”里下榻。那时候,汉口是座繁华大城,夜夜笙歌杂闻、舞影婆娑,可谓烟花干云、春风胜游之地。可是,周先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着晚间决不外出参加交际应酬的生活习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这在当时就被汉口上层交际界传为美谈。
1938年不仅是武汉这座大城的一个难忘的年份,也是周苍柏先生蒙受了深重的家国之痛的一年。这年春天,他的次子德佑,一位卓有才华的小提琴手,随“拓荒剧团”到鄂西北山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时染上恶疾,不治而夭折,年仅18岁。8月,武汉沦陷。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周苍柏,只好把长女小燕、长子天佑送往异国他乡巴黎去学习音乐。山河破碎,亲人离散;故园有情,夕阳无语。周苍柏送走一双儿女后,便忍痛收拾行装,和夫人一道离开了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汉口,买棹西去重庆,一去就是漫长的八年。这期间,他的长子周天佑在1940年也不幸病亡于战火纷飞中的欧洲。
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一家得以团聚,他和夫人、女儿迁到了上海和北京定居。留在汉口的公馆,则捐赠给了地方政府,先是做了武汉驻军某部的干部宿舍,后来又几经辗转,早已物是人非。现在这座老公馆的产权,已经分属当地的几户人家了。所幸的是,这座老公馆并没有在历年的旧城改造中遭到拆毁,有关部门还在院门一侧钉上了刻着“周苍柏公馆,武汉市历史保护建筑”字样的铜牌。这让我想到了罗斯金的《建筑的七盏灯》里的一句话:“毫无疑问,那些带有历史传说或记录着真实事件的老屋旧宅,比所有富丽堂皇但却毫无意义的宅第更有保护和考察的价值。”“霭霭芳园谁氏家,朱门横锁夕阳斜。”时代变幻的风雨和人事代谢的沧桑,无情地涤荡过一座座曾经繁华的深门大宅。高悬的月亮,虽然还是过往岁月的那一轮,但弦歌消逝,华筵已散。大树依然在,老屋已无言,多少楼台水榭,都隐入了旧时光的苍茫烟雨之中,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70年2月,一个寒冷的大雪天里,一代爱国名人和银行巨子周苍柏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斯人远矣,但是,体现在周先生和他的儿女们身上的民族大义与家国之梦,却永不泯灭,将与“海光农圃”和“苍柏园”边苍翠明丽的湖光山色同在。
(来源:湖北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