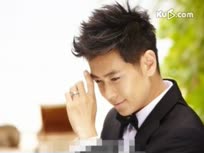◆夏祖丽
吴贻弓导演《城南旧事》
一般来说,孩童对于人生善恶固然需要指引,《城南旧事》里英子眼中的小偷、把亲生孩子卖了的黄板牙、做过人家姨太太的兰姨娘,还有惠安馆里的疯子,他(她)们在成人眼中各有不同个性和故事,但林海音在下笔时,却没有黑白分明、善恶立现地去评判事情,而是呈现出人在没有办法时的弱点。这样的作品,往往比伦理道德教条式的写法感人得多,也更引人深思。事实上,孩童探触人生的能力远超过成人的预期,他们往往在体验一件重大的事件后,快速成长,体会到人生的复杂与多变。林海音本人就是如此,在十三岁失去父亲的那一天,她就提前长大了。
一九八三年,上海导演吴贻弓把《城南旧事》拍成了电影。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八个样板戏使人倒了几年胃口,这时一部写老北京、写古老中国人的亲切人性的电影,一下子使整个中国轰动起来。人们心想,原来我们还有过这样美好的日子啊!《城南旧事》感动了电影院中无数的观众,林海音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台湾作家。《城南旧事》不但在中国大陆各地放映,还在世界上四十七个国家放映,得到许多国际大奖。包括: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鹰奖(一九八三年)、第七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一九八四年)、第五届厄瓜多尔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一九八八年)。这部电影也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作曲奖(一九八三年),导演吴贻弓获得最佳导演奖,饰演宋妈的女演员郑振瑶获得最佳女配角奖。此外,获得一九八四年度香港十大华语片奖,《文汇报》与《文汇电影时报》合办的“文革”后十大最受欢迎影片之新时期十年电影奖,吴贻弓获得该活动的导演荣誉奖。
正如作家文洁若女士说的:“它使人耳目一新,仿佛是闷室里打开了一扇窗户。”旅居温哥华的中国大陆作家丁果也说:“《城南旧事》这部电影,把中国人饱受阶级斗争摧残而冷漠的心灵暖暖地燃烧起来。在台北街头匆匆而过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尽管林海音女士在他们身边生活了几十年!”
导演吴贻弓表示,《城南旧事》电影的拍摄曾经过一些周折。早先,导演伊明在社科院台湾文学研究所看到了《城南旧事》这本小说,很喜欢,于是改编为剧本,想拍成电影,但一直没实现。后来伊明就将剧本交给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陈荒煤觉得很不错,就推荐给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觉得这是本好书,值得拍,就把吴贻弓找了去,吴贻弓当时刚刚开始独立导演,拍了《巴山夜雨》及《小花猫》两片,吴贻弓看了剧本后,要求看原著。看了原著后非常喜欢,表示如果要他拍,他要重新编,回归原著。后来吴贻弓重新写了一份导演工作本,为了尊重前辈,编剧仍用伊明先生的名字。
北京,国王的梦境
林语堂说过:“北京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一九三六年,林语堂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之前,特地再去北京一次,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城市比北京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林海音受到日本老舍研究会藤井荣三、中山时子等教授的邀请,到日本关西大学该会年会上演讲《城南旧事》里的旧北京。林海音告诉与会的人,她心目中的北京三宗宝是:“城墙、天桥、四合院;骆驼祥子满街跑”。《骆驼祥子》是极熟悉北京民俗风情的作家老舍以北京为背景所写的名著,也是林海音很喜欢的一部小说。老舍的另外一些书《四世同堂》、《离婚》、《老张的哲学》也都是以北京为背景。马森教授曾把老舍笔下的北京和《城南旧事》里的北京做过比较,他表示老舍把北京的大街小巷、春夏秋冬、达官贵人、地痞流氓、教员学生、贩夫走卒差不多都写遍了,老舍对北京所知之深、所见之广,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与之相比了。但是老舍偏偏没有看到林海音所看的、没有写到林海音所写的。林海音是从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来看北京,她的视野、见地和情感,与成人的老舍大不相同。如果说老舍有关北京的小说是社会性的、批评性的和分析性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则是个人的、感情的、综合的。
林海音通过英子的眼睛把北京城南的风光穿插其间,给全书一种诗意。评论家认为,那座城和那个时代变成一种亲切、包容的角色,《城南旧事》若脱离了这样的时空观念,就无法留下永恒的价值了。
中国自古以来才子出江南,北京虽是座文化古都,但北京的文学家却不多,像写北京的丁西林、老舍、曹禺、张恨水、萧乾,甚至林海音,原籍都不是北京。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九九九年年初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年的北京人穷人占的比重较大,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穷人。老舍是个穷人,他写的也是穷人。他说:“《红楼梦》写的是北京上层阶级的大家庭,曹雪芹了解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人的生活,因此《红楼梦》出了彩。《骆驼祥子》写的是北京下层阶级,那样一个劳苦大众的人力车夫,因为老舍了解他们,写得好,所以也出了彩。而林海音先生是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写北京人的生活。她在这个层面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反应,就上来说,可以观察自己的父亲,也就是知识分子;就下来说,可以观察老妈子、农民、小偷。所以她往上也能够一够,往下也能够一够,眼界比较宽阔,取材也比较广泛。这个阶层的北京在文学上原来是空白,因此《城南旧事》这本书在文学上有一定的分量、地位和价值,毕竟这个角度很重要。《城南旧事》保留了那个阶层北京的生活风貌,而且它里头的民俗部分也很重,这使她的作品有很大的乡土气,乡土气是林先生作品中很重要的气氛,有一种味道,看她的东西能闻出那种味儿。”
北京外语学院教授、语言学家夏祖煃表示,在老舍写了《四世同堂》以及曹禺写了《北京人》之后,这个中间是一段空白,这时突然有一个不带政治性、不喊口号,讲北京市民生活的《城南旧事》出来。而《城南旧事》里写了很多老舍与曹禺想写而没写的人物,像疯子、老妈子、小英子等。他说:“你一想到英子住的晋江会馆,就会想到旁边也许可能有一个洋车厂,而这洋车厂里,很可能骆驼祥子就在那儿拉车。从晋江会馆往南走,那可能就是《骆驼祥子》小福子上吊的树林。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把这些都串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当时大陆上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很感动,因为它很真实,更难得的是它保存了那个时代的语言,非常质朴、非常透明,又非常道地的北京话。它就是当时穿白布褂儿、黑裙子,在街上走的中学、小学女生说的话。人说语言大师、语言专家的,其实林海音才是语言大师,她的语言精练、纯朴而平易近人。今天北京胡同里学生间的怪话很多,现在的语言在变。但《城南旧事》里保留了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人的语言,这点很重要。”
作家铁凝也为《城南旧事》叙述语言的质朴、简洁和温暖的幽默感动。她说:“文笔细腻清秀或真挚热烈都不困难,但幽默却是最高形式,我喜爱林海音这也是一个重要缘由。”
作家萧乾晚年曾与妻子文洁若合作翻译了《尤利西斯》(Ulysses,1922)这部巨作。一九九九年文洁若女士在萧乾先生故世后在北京寓所接受访问时表示,《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James Joyce),二十二岁就离开他的家乡爱尔兰都柏林,在法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埋骨瑞士,终身都没再回过爱尔兰,但他毕生写作却以他二十二岁之前居住的故土为主。因此有人说,倘若都柏林从地球上消失了,仍能根据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来重建这座城市;爱尔兰、法国、瑞士都以“拥有”乔伊斯为荣,不管他的作品写的是什么地方。而林海音远离她住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北京,在台湾怀着深切的思念之情,描绘出一幅幅古老北京的民俗画和风景图。文洁若说:“爱尔兰人注意保存古迹,近一个世纪来,都柏林的变化不大,可是北京城,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要想重温一下这座文化古都的风貌,还真得读《城南旧事》呢!”
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的:“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
(来源:新民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