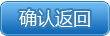专业芭蕾舞老师在给这些农民工的孩子示范舞蹈动作。
●“深圳是个文明的城市,我们想让有钱人的后代在跳舞唱歌的同时,也让穷人的孩子有机会去跳舞唱歌。”关于自己的初衷,“小花朵芭蕾舞团”团长王亚珺有一句朴素的概括,“我想通过‘小花朵’,让社会掌握权力的人、有钱的人,能够关注劳工阶层的人。他们的孩子不该失去享受艺术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小花朵芭蕾舞团唤醒了一些艺术天分很高的小舞者。在舞蹈教室里经过训练的他们,开始有了小小的“虚荣”和骄傲。“从没想过和芭蕾有缘分”的父亲看到女儿跳舞的样子,明白了女儿的天分所在。
关于芭蕾,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有句常被引用的诗:“让她跳完她的舞,让她跳完她的舞!现实太狭窄了,让她在芭蕾舞中做完尘世的梦。”
一个企业家用她的一点力量想要证明,无论家境如何,有天分的孩子应该拥有做尘世之梦的可能。
上月底,33个跳芭蕾的孩子来到深圳音乐厅,与深圳交响乐团同台,表演了7分钟的《胡桃夹子》选段《花之圆舞曲》。主持人介绍,这些孩子全部来自深圳劳务工家庭,舞团的名字叫“小花朵”,这群孩子正式习舞时间才两三个月。
在舞团发起人兼团长、深圳市假日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亚珺的资助下,“小花朵芭蕾舞团的孩子们免费参加训练,由学校提供免费场地。去年7月至今,已经有140多个孩子成为团员。舞蹈团在5个学校设有驻点,其中,侨香学校、华丽小学、华英学校和草埔小学都位于罗湖。下月,“小花朵”将开进梧桐小学。
“劳务工里不乏有艺术天分的孩子,因为家境拮据,父母只能供他们读书,没有能力给孩子多一点机会进行艺术熏陶,而孩子不论出身,天分都应该早一点开发。”王亚珺说。
芭蕾如何进入与之不甚“搭调”的城中村?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反差?又在这些家庭中激荡出怎样的涟漪?
缘起 挫折中前行的公益探索
芭蕾舞打开城中村的大门,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小花朵芭蕾舞团的初创阶段是摸黑探路的过程,有不少阴差阳错的际遇。
刚冒出帮助劳务工子女学芭蕾的想法,风风火火的王亚珺就马上联系了深圳福彩中心,经他们介绍,两天后就找到了龙岗区平湖镇的新南小学,学校一天之内联系了38个孩子。舞团对第一批孩子来者不拒,“孩子都已经来了,不要伤他们自尊”。好在这些孩子都很符合芭蕾的最基本要求——腿直。
孩子们被分成两个班:大班最小的10岁,小班最小的6岁,每天下午分别在新秀小学不同的楼层训练5小时。大班后来学了《天鹅湖》,小班排了《万泉河水清又清》。
排练一开始就遇上了硬件设施的麻烦:学校7楼厕所上下齐堵,老师和孩子上厕所要辛苦爬楼。为了重装厕所,王亚珺出了3万元。一个暑假里,公司就花了将近10万元。项目的运营和经费的管理都令她困扰。
更大的打击是,某天教室里来了几个舞蹈专家,看了一圈后直言不讳地说:“你这哪里是芭蕾?就是民族舞。”
8月23日,舞团给每个孩子发了结业证,还举行了汇报演出。王亚珺“想把这事了了,不想做了”。没想到的是,舞蹈教室挤满了家长,都要来看孩子跳舞。在这次演出中,王亚珺还帮一对姐妹实现了梦想:有了弟弟之后,父母就冷落了她们,她们跳舞的理由是希望爸妈能抱抱自己。
停课的时间里,王亚珺开始四处征询建议。他们找到了深圳市福彩中心作为主管单位,并给舞团定名为“小花朵”。为了得到更多认同,王亚珺决定让孩子们多参加汇报表演。龙岗区平湖街道办邀请舞团参加凤凰社区的演出。9月底,课程重新开始,舞团在今年1月30日劳务工返乡前举行了汇演。
王亚珺也确定了“小花朵”不同于一般芭蕾舞班的训练方式——倒训。孩子们先排完整的舞,再练习基本功。“事实证明,这些孩子为了把舞排好,会更刻苦地练基本功。”曾在辽宁省芭蕾舞团担任专业舞蹈演员的常巧莉老师说。
重振旗鼓后,“小花朵”开始惠及更多的孩子。通过与罗湖区政府联系,草埔小学、侨香学校、华丽小学相继成为“小花朵”的驻点学校,本月中旬,梧桐山下的华英学校成为“小花朵”的第五个据点。团员们每个星期有两天要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训练。
来自不同的学校的孩子,父母都是在深劳务工,他们中有清洁工、技术工、促销员、洗头工人、洗碗工、的士司机,果蔬摊档或肉菜店的售货员——包括了种种人们能想到的不可或缺的基层职业。参与培训的芭蕾老师增加到了4个,受惠的孩子也达到了140多个。
迟来的起点 痛并快乐着
团员们的年龄在8到11岁之间,又以9岁、10岁居多。而10岁,已经是许多有志于舞蹈生涯的孩子去考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年龄。
许多团员都符合芭蕾的要求:清瘦的脸蛋和身板,以及细长的腿。但是跟那些从更重视艺术特长的家庭走出来的孩子相比,她们更晚觉察到自己的美。因此,要把韧带拉开,达到“开、直、绷、立”的要求,得吃更多苦。
周洋老师觉得,“小花朵”的团员教起来相对容易,出成绩快。她平时也带一些兴趣班,常遇到因为太苦而退出的孩子。而这里的孩子对练舞的机会更珍惜,“很少有孩子回家跟父母叫苦叫累,家长也很少会说,孩子太辛苦,不训练了”。
不可避免地,疼痛与练习如影相随。在草埔小学的舞蹈教室里,周洋走到一个孩子身边,把她的腿往更直的地方掰了掰。“疼吗?”周洋问。“疼。”那孩子短促地应了一声,又继续忍耐着。压腿时、换腿时,都可以听见此起彼伏的哼哼声,又有节制地齐齐止住。
提到“踩胯”,许多孩子都会露出庄重而又害怕的表情。这是一场撕心裂肺的仪式,却是芭蕾必须的训练。
记者在侨香学校的舞蹈教室见过一次“踩胯”。孩子们挨个中断练习,怯生生地走到扶栏下躺稳,分开两腿,大腿和小腿摆成一个直角,老师撑在栏上,把孩子们的膝盖踩到最贴近地面的程度。持续的时间是从1数到20。随着忍耐的极限到来,他们会越数越快,语调也越来越高。
“我想当舞蹈家或者舞蹈老师”,一个孩子像专业舞者那样老道地说:“不吃苦练不好”。有的女孩一边压腿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还争着展示自己感觉最痛的地方。
“坚强”对这些孩子来讲并不是困难的要求,他们提得最多的还是“开心”。在草埔小学,没能入选“小花朵”的孩子对团员们的经历很是羡慕,常三三两两等在教室门口想要加入,有男孩也有女孩。关于跳舞,10岁的吴欣童说了一番很有哲理的话:“我喜欢芭蕾,因为跳舞时我很开心,有没有观众都没关系,我喜欢这件事本身。”
芭蕾舞教室 突然发现自己的美
小花朵芭蕾舞团唤醒了一些艺术天分很高的小舞者。但王亚珺也知道,“100个孩子里,能有一两个成为专业舞蹈演员,我做梦都要笑醒了”。她更希望的是提高这些孩子的艺术修养和个人素质。
“小花朵”驻点的学校,学生大都来自条件较差的城中村、插花地。选拔团员时,孩子们一波波进来拉高裤腿,工作人员发现,“几乎没有一双腿是光滑平整的”,到处是蚊虫叮过的包、深深浅浅的瘢痕,以及磕碰过后的伤疤和淤青。
这些孩子被按照脸型、腿型、身体比例接受选拔,但过程比真正严格的芭蕾选拔要宽松得多:没有皮尺,全靠目测。毫无疑问,最后进入舞团的孩子,是周遭同龄人中最符合芭蕾要求的,除了表情——他们的不自信写在脸上。当被王亚珺问到“谁觉得自己是美女帅哥”时,孩子们低下头一声不吭。不少团员被选进“小花朵”时,是“一副弯腰驼背的样子”。
不过,在舞蹈教室里经过训练的他们,开始有了小小的“虚荣”和骄傲。
在教室里,女孩们一边练习,一边偷偷打量镜中的自己。走出教室,家中的镜子也常被“征用”。有一位在水果批发市场工作的家长说,女儿回家后总是对着镜子练习跳舞时的微笑,以前鲜有笑容的她发现自己脸上竟然有个酒窝。
课间休息时,她们娴熟地替彼此盘好头发,再昂起头照照镜子。很多女孩就连趴着聊天也挺直了脊背,把自己熨帖在地板上,只抬起肩膀和头。男孩子则要调皮很多,对那些优美的动作也不太上心,在教室里疯跑大吼着。不过,他们跳起舞来的时候却也有模有样,老师形容他们“翘着小屁股,走路一夹一夹的”。
记录名字时,气氛最热烈。孩子们默契地挨个贴到记者身边介绍自己,希望名字能被准确地写在纸上,有的孩子还招呼一旁练舞的同学过来,生怕他们被忽略。
一个女孩从书包里翻出演出照片,递给记者看。相纸的边缘微微卷起,似乎被随身带了很久。女孩们一下子聚拢过来,指着照片里一颗颗豆子那么小的脑袋说:“这是我。”
镜头中有他们所渴望的自我。王亚珺和她的同事们给舞团做了许多海报,不久前,一位小团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了自己近期的梦想:“有一张我的个人海报。”
舞鞋、服装和白色袜子是被特别珍视的物品,不仅仅因为他们只有一套。一个女孩告诉记者,老师说“跳芭蕾的不能穿得脏兮兮的,要像公主一样才能来上课”,每周两堂课之前,她都自己洗舞蹈服,又叮嘱妈妈替她收下,免得阳光晒褪色。一位妈妈说,女儿坚持要她“用沐浴露洗裙子”,怕洗衣粉把裙子洗坏了。
两个故事 回到城中村的“小花朵”
芭蕾课上,孩子们随着交响乐做出优美的动作,眼前是开阔明净的教室和随处盛开的纱裙。下课后换回校服,记者与一些孩子一同走在密集迂回的巷弄之中,这里有大功率音箱和迪斯科音乐、聚满了人的台球桌,以及投币游戏机。孩子们面对着两个鲜活却迥异的世界。
走上一段阶梯,来到草埔的生活区域。眼前的旧小区有上世纪80年代统建楼的特质,因为房租便宜而云集了大量外来务工者。10岁孩子陈怡和苏华的家都在这里。李亚莎说,这几乎是所有“小花朵”生活的典型状态。
陈怡的家在二楼,两室一厅的潮湿房子里,她跟哥哥、双胞胎弟弟、爷爷、奶奶同住一屋。父母经营一家60平米的杂货店,一家七口以此为生。爸爸守在店里,几乎从不回家。
屋子的一面墙贴满了陈怡的各种奖状,在舞团里,她也是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女孩, 还担任草埔小学28位“小花朵”团员的班长。一张七人海报中,她斜侧着身子,绷起一只脚尖,手腕很有力量地交叠在一起,表情严肃中带着一抹浅笑。和其他孩子相比,她似乎对摄影师想要捕捉什么更有直觉,也更自信。
不过陈怡的艺术特长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哥哥对跳舞的妹妹一无所知,他边打游戏边告诉记者,妹妹“就像个男的一样”。
陈怡的妈妈周女士倒是表达了对女儿的支持。她平时没有时间听音乐、看电视,也没有时间辅导孩子们的功课,更没听说过芭蕾。但是,今年1月30日,她在深圳大剧院音乐厅舞台上看到了女儿,第一次化妆的陈怡看起来很美。
提到芭蕾对于自己家庭的意义,周女士反复回答“让我们开心”。到了临别时,她才叫住记者,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能告诉我,芭蕾到底是什么,学芭蕾对我们孩子有什么好处吗?”
另一类家长却格外清楚“小花朵”对孩子的意义,例如小男孩苏华的妈妈陈女士。在儿子一度想要退出时,陈女士跟儿子谈了很久的心,“这么好的机会,不要放弃”。她小时候也梦想踮起脚尖旋转,但从没想过自己的儿子能像这样跳舞。她把小花朵芭蕾舞团的事说给肉联厂的工友听,大家对芭蕾没有什么了解,却都感觉这是好事,“你儿子真优秀,什么活动都有他参加”。
未来 希望得到更多支持
芭蕾是苛刻的艺术,对许多劳务工家庭来说,也是奢侈的学习。
在舞蹈教室外探视时,吴欣童的妈妈黄女士就在懊悔,没有早点把女儿送去习舞,“让她现在多受了压腿的罪”。上幼儿园时,每次跳团体舞,欣童总是学得比其他孩子快,节奏感也更强。不过家里并不宽裕,欣童的舞蹈梦在小学后就中断了,直到“小花朵”的出现。
尽管每个家长都很支持孩子去“小花朵”学芭蕾,但心态却各不相同。有家长没来得及对芭蕾了解更多,只是感觉孩子入选很光荣,也因为课程免费而感到轻松和欣慰;另一些家长则是抱着替孩子圆梦的心情,也在未来的经济负担上做了一些打算。
王亚珺介绍,小花朵芭蕾舞团目前只针对小学,不过以后也会考虑为天赋高又有意愿的孩子提供继续学习的帮助。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这也意味着,无论如何几年之后都会做出选择:是否让孩子继续学芭蕾?在深圳辛苦打工的父母各有各的答案。
说起这件事,周女士有点犯难:本来就对芭蕾没有什么概念,即便是城中村每节课45元的简易芭蕾班,也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不能承受的负担。
不过,侨香小学张乐瑜的父亲却十分坚定。“从没想过和芭蕾有缘分”的他看到女儿跳舞的样子,就明白了女儿的天分所在。“她瘦小,身子柔韧,跳舞特别会找感觉,如果以后孩子有兴趣,我一定会培养她,再怎么样也会想办法凑钱,不要担心”。
关于自己的初衷,王亚珺有一句朴素的概括,“深圳是个文明的城市,我们想让有钱人的后代在跳舞唱歌的同时,也让穷人的孩子有机会去跳舞唱歌。”她给废品收购站工作人员的女儿联系过越剧艺术家拜师学艺;以后还希望跟深圳交响乐团合作,给劳务工子女办小型弦乐团,请人资助孩子们买琴和学琴的费用。
目前小花朵芭蕾舞团有近150位团友,王亚珺计划把他们都家访一遍,记下他们的家庭遇到的困难,“通过小花朵芭蕾舞团这个品牌,去寻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
“希望到2015年,我们能帮助300个深圳劳务工的孩子,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王亚珺说。近一年来,单是为每个“小花朵”的服装、演出和训练所支付的费用,就达到约4500元,王亚珺表示这些费用“目前还能担负”,但未来希望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王亚珺说,除了现有的四名兼职爱心老师之外,公司还准备聘请两位全职的芭蕾老师,其中一位来自俄罗斯芭蕾舞团。
“我想通过‘小花朵’,让社会掌握权力的人、有钱的人,能够关注劳工阶层的人。他们的孩子不该失去享受艺术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她说。
(为保护受访孩子隐私,“小花朵芭蕾舞团”团员均使用化名。)
“小花朵”的公益总动员
链接
“在中国,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应该打通各路人脉来做公益”,王亚珺说,这是她近一年来的体会。
送一群只学过两三个月芭蕾的孩子登上深圳音乐厅舞台,参加深圳交响乐团的“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许多人听了都觉得不可理喻。不过王亚珺非常坚持:“这些孩子能不能成为舞蹈家是一回事,但我们要给他们创造登台机会。”
她甚至告诉工作人员,“我帮你们卖票,我们的孩子要上台演出”。借由深圳本地媒体和公益人士牵线,华润银行深圳分行、北方工业深圳投资公司、清水河街道办都资助购买了当晚的演出门票。
当天晚上,孩子们的另一次表演机会来了。墨西哥驻广州总领馆正好在深圳举行文化旅游推介会,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对王亚珺说:“我愿意给你5分钟时间,讲讲小花朵的构思和未来计划。”听完发言,他表示今年秋天会邀请孩子们去广州参加领事馆的慈善演出。
王亚珺说,自己的团队正在不停地给孩子找演出机会,“几个学校加起来能有13支舞蹈,可以做晚会,不做商演,只做公益演出”。暑假里,驻港部队和平湖的防化部队都有邀请孩子们参加军民建设演出的打算。王亚珺还有更大的想法:编出具有深圳特色的少儿舞蹈,请俄罗斯老师强化训练,让孩子们上春晚。
演出只是“小花朵”芭蕾生涯的一部分,而另一个重要部分,则是每周两次的排练。王亚珺说,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给予了她很大支持,并且无偿提供场地。
去年,清水河街道办负责人在听完“小花朵”的故事后,把几个校长请到了办公室。“不能耽误这么有才华的孩子。有公益人士愿意帮忙,咱们干嘛不好好配合呢?”这番话说动了校长们。随后,草埔小学、华丽小学两所公办学校将学校的舞蹈室无偿提供给小花朵芭蕾舞团。
民办学校的条件比较差,侨香学校虽然有舞蹈教室,但房顶很矮,且没有空调。校长被“小花朵”的工作人员感动,开始游说投资方的董事长:“你投资万把块钱,舞蹈教室就不会荒废,公益人士就能替你把孩子培训出来。”这番话促成了孩子们练舞条件的改善。
爱心老师们的帮助,也让“小花朵”能够顺利开在各所学校。王亚珺说,有的老师就是想帮人,甚至提出分文不取来带芭蕾课,老师们所收取的学费也略低于市场价格。他们到偏远的学校去上课,甚至没向王亚珺要过一分钱路费,“就当是顺路给孩子们上上课”,梁子老师说。
策划/统筹:吕冰冰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来源:南方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