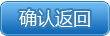石悦江
记得初次读梭罗的名篇《瓦尔登湖》是一个温暖而沉静的春天,久久沉思在澄明而幽静的文字中。
梭罗书中某些隐世哲学,成了他“游手好闲”、“冷眼旁观”的托词。1884年春天,梭罗和爱德华·霍尔(康科克德镇名门之子)在河畔森林煮鱼杂碎汤,失手酿成一场森林火灾。梭罗到镇上寻到救援后,并未去一同参与救火,却出乎意料爬到附近山坡上观看火景,此案最后定论为一场“意外”,梭罗在镇上的名声却终免不了镇民们诟病,书中虽反复告诫人与自然亲同一家,可当自然出现危难,作者本人却置之度外,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审视人对自然犯下的罪过。
人们以为梭罗是太超然了。但他忽视了这套隐世哲学并非人人可以生搬硬套,他劝说钓鱼伙伴约翰·菲尔德过节欲简朴的生活,他以为这样便可以让人摆脱痛苦,这就意味着舍弃一切物质上的需求,而对于菲尔德这样有家室、谋生计的穷苦人,要放弃生存的起码条件去追求精神的安宁,这可能吗?
《瓦尔登湖》记录有一张开支28元多美金的建房开支表,是梭罗亲手在湖畔造一所房子的全部明细,精细到一支粉笔的价钱。自耕的生活态度让人佩服,因在那种环境里一砖一瓦白手成家非人人可以办到。梭罗自谦公开这些清单是种罪过,可还是公之于世了,这样涓滴不漏的记录里除为达到成书的目的,是否也夹杂着夸耀的动机?
于是,一位评论家中肯而善意地指出:“想要隐士的声名却又不想过真正隐士的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梭罗的本意。”这值得读者细细反思,书中令人肃然起敬的“简朴,简朴,再简朴”的生活,梭罗并未真正实现。
回到初读《瓦尔登湖》时,读这样的文字会轻易爱上孤独的,没有工业社会烟火味的文字有种经湖水涤净后的芬芳,作者对隐居生活的构想,对理想独特的精神指向,对如何正确处理自然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如何在内心生活与尘世喧扰之间保持平衡,如何用一种自省而向上的朴素世界观求证生活的种种谜题提供了上乘的范本,历经百年仍不失很强的借鉴意义。
善意的读者,喜欢书中那个“冷傲孤远,犹如高寒地带秋日的天空一样深旷”的梭罗,而无意地忽视了这个真实的梭罗。《瓦尔登湖》无愧英文散文的杰作,作为“超验主义”代表作家,梭罗无法避开自身世界观与生活环境的局限。
还是要保存对《瓦尔登湖》的美好印象,不管它上空悬置的生活是否真有实现,逾越百年,人们心中共同的梦借此书启发,被一次次升华和冲击。我们虽不曾停止对精神与物质、自然与工业间尖锐冲突的积极反思与艰辛探索,但面对愈演愈烈的奢侈与贪婪、荒芜与消亡、虚无与冷漠,仍不由得嘘一口气,何时梭罗心中永恒的瓦尔登湖,到我们身上才能变为现实?不再是书中梦一样的自白?
而后,慢慢从书中走出,去发现文字背后的故事,才了然那只是梭罗心中的瓦尔登湖,而我们仍在间接地思索,或践行在作者书写的理想国的路上,任重道远。
书与作者间的关系应谨慎区分,尽信书不如无书。喜欢一部作品,容易变成对作者的盲目崇拜。
瓦尔登湖不是隐者的天堂,与新英格兰许多人迹罕至的湖泊相比着实逊色。它的扬名梭罗功不可没。《瓦尔登湖》已成为崇尚简朴、单纯,亲近自然,远离工业文明的一种象征。
两三年湖畔生活,梭罗并未全身心实践书中的隐世哲学。仍然每日往返于康科克德镇上,每日回家探望父母,享受琐细而幸福的家庭生活。他的小木屋,到访者不断,梭罗与他们互饮对谈,派对野餐,成立文人社团,并未与俗世生活孑然分离。
(来源:长沙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