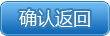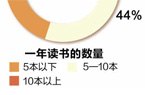|
张伯驹与潘素 照片均由楼开肇先生提供
 | ||
展子虔 《游春图》(隋) 张伯驹 捐赠
 | ||
陆机 《平复帖》(晋) 张伯驹 捐赠
【人物简介】
张伯驹 (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冻云楼主、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家、京剧研究家、词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因身出名门,多才多艺,儒雅风流,被时人与袁寒云、溥侗、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1937年正月,北平隆福寺街福全馆传出了余派老生的唱腔。而须生泰斗余叔岩并非台上的孔明,他与杨小楼、程继先、王凤卿三位名伶甘当绿叶,陪一位票友唱《空城计》。这场本为自娱的演出,作为佳话载入了戏曲史册。1956年7月,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一纸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赠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现存最古的墨迹 《平复帖》,能进入故宫博物院珍藏,也多亏了那场堂会的主人。这是一位不世出的奇人、怪人,书画、诗词、戏曲三个领域皆造诣不凡。有人说他荒芜正业,有人赞他傲视王侯,他则依然故我,笑骂由人。这份潇洒与通脱,为后人留下了谈资。他,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关于“民国四公子”的说法,版本不一,但袁寒云和张伯驹入选,允为公认。因二人均属中原子弟,且别号中都有云字,又有“中州二云”之称。所谓:“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张伯驹从小过继给伯父张镇芳,7岁入私塾,9岁能诗,享有“神童”之誉。成年后,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其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生性散淡的张伯驹厌倦军旅生活,便不顾双亲和众人反对,褪下戎装。1927年起,张伯驹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虽有这般头衔,张伯驹真正的职业仍就是玩。诚然,他玩出了风雅,玩出了学问,玩出了气节。这样一位玩家,在刘海粟笔下是“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那年海上花正开
提及张伯驹,不能不提他的神仙眷侣潘素,他们的恋情上映地就在上海。
“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嵌入“潘妃”二字的楹联出自张伯驹之手,这是他与潘素初见时留下的辞章,那一年潘素刚刚19岁。其父潘智合乃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其卖入欢场。潘素弹得一手好琵琶,人们称其“潘妃”。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结果就撞上了“潘妃”。惊鸿只一瞥,爱到死方休。初见潘素的张伯驹,惊其为天人。一位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已和潘素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孰料半路杀出的张伯驹,一下折服了美人心。潘素要悔婚易嫁,这可惹恼了臧卓。于是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张伯驹不惜屡险,在友人帮助下,成功带走潘素夤夜北归。这便是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社会新闻:一品香夜半抢“潘妃”。
张传綵是张伯驹和潘素的独生女,年过八旬的她坦言,对父母结合的事并不清楚。“从小家里有规矩,孩子不能过问大人的事,他们也从来不讲这些。但是我父母的感情好却是真的,父亲对母亲的呵护是令人羡慕的。”在张传綵记忆中,公子张伯驹会为潘素亲手煮咖啡,全力支持潘素的绘画事业。结缡后,潘素的潜能被张伯驹发掘出来,终成一代女画师。张伯驹填情词颇多,但异于袁寒云,他的情词只为潘素一人而写。潘素也成为陪伴他走完一生的女人,无论繁华抑或蹉跎。潘素生日,张伯驹写下: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二人结合40年后,张伯驹与老妻暂别,依然有款款深情的《鹊桥仙》相赠。“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浦江遭绑,北平典房
张伯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曾写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成了一家之主,可以自由支配财产。但当他拿一所大宅院换来一张轻飘飘的字画时,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母亲免不了唠叨、抱怨。家族之中,更有人斥责他为“败家子”。除了家族的压力,让张伯驹更痛苦的,是有时不得不眼看着国宝流失国外。他后来回忆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
为了留住一件国宝,张伯驹时常历尽艰辛,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他的收藏生涯中,最复杂曲折的经历,要属与《平复帖》的缘分。此帖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有“墨皇”之称,曾为宋徽宗收藏,此后多次转手,清朝成为雍正孝圣宪皇后的嫁妆,死前赏赐给儿子成亲王,成亲王曾孙载治去世时,其诸子皆幼,恭亲王被指派为监护人。大约在此时,恭亲王乘机将《平复帖》据为己有,后来就传给了他的孙子溥心畲。上世纪30年代中叶,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因之前溥心畲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流转到英国。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重蹈覆辙,急忙托朋友和溥心畲商量。溥心畲开价20万大洋,张伯驹根本拿不出。第二年,张伯驹又托溥心畲的挚友张大千致意,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心畲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年春节前,溥心畲母亲去世,急需大笔的钱。幸运的是,张伯驹此时正在北京,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张伯驹对此大为快意,“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然而,在动荡的年代,拥有《平复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张伯驹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但歹人最终没有放过他,1941年被绑架。绑匪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伯驹搞收藏跟别人不同,他是只进不出,收藏的都是珍品,一旦到手,决不出卖赚钱。如此一来,家里越来越空,根本拿不出那么多赎金,而绑匪后台竟是上海滩的杀人魔窟——汪伪76号总部。出于种种考虑,银行方面也拒绝帮忙。
万般无奈的潘素设法与绑匪沟通,得到看望丈夫的机会。张伯驹悄悄告诉潘素,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 《平复帖》,“那是我的命”。就这样,一直僵持了八个月,绑匪看实在要不来那么多,就答应降价,张家以20根金条了事。此后,张伯驹将该帖缝在衣服夹层,须臾不离身,悄悄运送到西安。
购买《游春图》,也是艺苑美谈。《游春图》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溥仪出宫时,被携至长春。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游春图》存于古董商马霁川处,便提出收购意向。马霁川开出800两黄金的高价,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隔几日得消息说经费不足,他只好先赶往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辅仁大学,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购画,不料马霁川提出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张伯驹无奈卖掉夫人首饰,才将国宝护住。
这两件事被收藏界看成“二希合璧”。而李白的《上阳台帖》进入故宫,也与张伯驹有关。1953年大年初一,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给张家送来火腿、糕点、白酒等四色礼品,张伯驹感激万分。“君赠我以木瓜,我还君以琼瑶。”张伯驹把自己珍藏的唐代李白手书《上阳台帖》回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称:“连城之宝,不敢归诸己手。”将它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在张传綵眼中,父亲从没用金钱去衡量艺术。“他是这样想的,这是历史文物,我们中国人应该是把它留给子孙后代。虽然这个东西是我买的,但是不能为我个人来欣赏。要为子孙后代来欣赏,知道伟大的祖国,她的文化是什么,艺术是什么。”
一出戏罹祸,一幅字复起
在张伯驹的眼睛里,艺术是纯粹的,不能有半点杂质。
除却书画,另一门令张伯驹倾注毕生的艺术是京戏,他以爱戏享名,也因爱戏遭难。上世纪50年代初,戏曲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改戏、改人、改制,让漂泊江湖的艺人脱胎换骨。在张伯驹为京剧的前途忧心忡忡时,一个消息振奋了他。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传出信息,“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张伯驹觉得该有所作为了。为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开办戏曲讲座,举行义演。张伯驹从纯艺术角度考虑,选择了三出剧目,意在让老艺人的绝活重见天日。
问题就出自剧目上面。张伯驹选的三出戏分别是《宁武关》、《祥梅寺》和《马思远》。《宁武关》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拿不动《宁武关》的。《祥梅寺》是丑行的开蒙戏,舞蹈身段实在漂亮。从艺术上看,张伯驹的选择是大家风范,但他全然不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物?还有《马思远》。《马思远》,一名《海慧寺》,清末实事,是一桩因通奸引发的凶案。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张伯驹找到擅演此戏的筱翠花,二人一拍即合。
当时《北京日报》披露了这一消息,并说报社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然而,当天下午,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解禁,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不认可这样的决定,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竟说了这样一段话:“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后来,有关方面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不满意。经此一番周折,张伯驹成了文艺界第一个右派。
上世纪60年代初,经陈毅推荐,张伯驹与妻子远赴吉林博物馆任职。吉林省地处关外,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比拟。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当时吉林省委某负责人对吉林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甚为抱憾,张伯驹闻言又捐献了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至此,这位书画第一藏家片纸皆无。
1967年,张伯驹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到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年近古稀,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风雪夜里,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原有的住房变成了大杂院,夫妇俩靠亲朋接济勉强度日。1972年,患难之交的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被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赞写得好,并询问撰联者为何人?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正式落户北京。
冬去春来,获得平反昭雪的张伯驹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他想为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1982年正月,张伯驹突然患病被送进北大医院。2月26日,乘鹤西游。
最后的公子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1961年初,张伯驹即将出关之际,陈毅送来这首诗以壮行色。张伯驹一生结识显宦无数,但在他眼中只有朋友和知音,多么耀眼的外在光环,张伯驹都视而不见。当年,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督抚华北,辖区内几个市长出缺,宋哲元让张伯驹随便挑选一个赴任,张伯驹听闻掩耳疾走。对于达官显贵的骄横,他也不惧嗤鼻冷齿。抗战期间,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来西安造访的蒋经国举行宴会,张伯驹应邀作陪。他看不惯蒋经国的“太子爷”做派,鼻子里哼出一声:“黄口小儿,何德何能,在此坐大。”蒋经国含怒询问祝绍周:“此人何方神圣?”不待祝绍周为他打园场,他倒抢先自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张伯驹是也。”
抗战胜利后,古董商郭昭俊把《三希堂法帖》送给宋子文。宋子文大喜,指示故宫博物院以十万美金买下郭昭俊非法占有的古瓷器,并任命他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张伯驹闻讯,挥笔写出《故宫失散书画见闻记》。宋子文闻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将原物奉还,由中南银行保管。
身处逆境,张伯驹从来也是坦然视之,好像一切于己无关。张传綵记得,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让他们划清界线,自己感觉不服。可是张伯驹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我会原谅别人。只要我自己没有亏待党。”
与人交往,张伯驹总是表现得不亲不近,但又常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张家与袁世凯是姻亲,但始终没什么来往。“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他宴宾客,眼看着他楼塌了。”昔日的“大太子”袁克定落魄之际,并不熟络的张伯驹找上门来,把他们夫妇接到自家供养,直至天年。在王世襄记忆中,自己当初为研究《平复帖》造访张家,张伯驹一开口吓了他一跳。“在这哪能看得完,拿回家看去。”千金不换的国宝在王世襄家中放了一个多月,他才得以写出《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在周汝昌记忆中,张伯驹从没说过狂话,毫无狂气,温文尔雅。
公子哥在人们的印象中,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当下,“X二代”屡屡挑战底线,富家子弟成了社会痼疾。但张伯驹的存在,让公子的另一种含义,得到了诠释。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生前最后的住所,如今已被改造为“张伯驹潘素纪念馆”。张传綵说,自己开办这个纪念馆,反对的声音很多,但坚持这样做,就是想守住父亲这种精神。“有钱的大少爷多少人吃喝玩乐,为非作歹,在那个时代我父亲没有像他们一样。他一生都追求高雅的品位,高尚的品格,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还需要这样的公子哥?”
记者在穿越的恍惚中,拟就此文。停笔掩卷,泡上一盏香茶,听着余派《二进宫》的录音,这段词似乎是为张伯驹所作:弹一曲高山流水琴音亮,下一局残棋消遣解愁肠。写几幅法书精神爽,巧笔丹青悬挂草堂……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