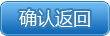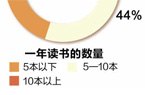田沁鑫(左)与秦海璐(右)、袁泉在《青蛇》排练中

田沁鑫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亚洲当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她的作品以对中国传统题材和世界名著的全新探索,对现当代社会话题的敏感捕捉,和当代艺术观念和东方美学相融合的舞台呈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在国际戏剧领域亦有影响。
代表作品有:话剧《生死场》、《红玫瑰与白玫瑰》、《四世同堂》、《风华绝代》、《赵氏孤儿》,昆曲《一六九九·桃花扇》等。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江雪文
图/受访人提供
在当今中国话剧舞台上,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无疑是极为引人瞩目的一位。她喜欢改编经典作品,将文字变成活人的艺术,在以男性导演为主导的戏剧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今年3月,田沁鑫最新话剧《青蛇》在香港艺术节进行首演,引起轰动,随后的一路巡演亦是好评如潮。6月27日到30日,这出戏终于要在友谊剧院与广州观众见面了。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田沁鑫说,《青蛇》是她创作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部,从最初的意念萌动,到最后成品,整整耗去十年时间。
《青蛇》台词
因为有缘……缘起缘灭,有因有果,成住坏空。
做人是不是就要形单影只,是不是就要自己面对了。我一天比一天聪明了,真是悲哀。
我只想得到人的眼泪,人的头脑,和一颗人的心。
男的什么都不会干。
不知是慈悲还是恻隐,烦恼即菩提。
追逐快乐本无过错,人人都希望生活安逸,情感满足,却把所有不快乐都当做不好的,想要千方百计逃避它。
我不退转,我的爱,万劫不复,永不止息…
我怦然...不能心动!
生理上的劫数比心理上的劫数更直接。
我知道人间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完美,但作为人妻,我只想一力承担。
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后之患。
一生一世很长,姑娘不可当真。
我向前走,这就是人间。
谈经典改编
找到高于原著的立意
&从不逡巡于儿女情长之间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一直喜欢改编经典?其中的挑战和乐趣在哪里?
田沁鑫:我一直在坚持排演一些中国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瑰宝,是能通过舞台上的立体呈现传递给观众的。文化不是单纯的知识掌握,它是一种活法儿。我的话剧是以情感为纽带,勾连起观众情感。戏剧的内容必须是有品质的,形式则应该不拘一格、多种多样。 我在创作过程中,会使用快速的节奏,用一些观众可感可知的表现形式,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不会觉得距离遥远,不会觉得无趣,这样更容易让年青一代认同我们的文化传承。
事实上我每次解读经典的时候,都要找到小说之上的一个立意,依托于小说而又高于小说。比如《四世同堂》,平民史诗,老舍先生为什么没叫它《八年抗战》?这还是从一个家文化、民族性上来说的。《青蛇》也一样,它给了我一个人、妖、佛三界的认识,那么我就照着这个认识来改编它。
羊城晚报:您说从改编话剧《生死场》开始,到《赵氏孤儿》,到昆曲《1699桃花扇》的筹备,一直处在男性叙事角度,您从小也不重视自己的性别。
田沁鑫:我的作品一贯以大胆、热烈的“力量”型面对观众,这来源于我的“中性视角”。我与其他女性导演的区别在于,从不逡巡于儿女情长之间,而是将艺术创作的视角投射到更为微观的心灵隐私,及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
谈《青蛇》
妖性也是人身上共有的
&我做这个戏后反而有一点入世
羊城晚报:《青蛇》这出话剧从最初的念头到今年的演出花了很长时间。
田沁鑫:2002年左右,李碧华希望我能改编《青蛇》,那时我觉得两个女人站在台上从头说到尾“嘶吧嘶吧”的,难有力度。当时的赵有亮院长说这是情欲的戏,如何能够从里边升华出来,好像大家都还没这个能力,于是就放弃了。但我心里还是稍稍有点不平衡,放弃这个想法后的某天,我在厨房里做饭,一边跟我的闺蜜说,我要做不可能制作成情欲交缠的戏,我可以做成人佛妖三界——这个灵感是十年前的了。
2000年我开始接触藏传佛教和僧人,一直到前三年接触到汉传佛教的大德高僧,有的方丈住持跟我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从他们待人接物和气质上感知到佛教的光芒。通过跟他们聊天,我潜移默化学到一些东西。所以《青蛇》这部戏确实融入了我这些年的思考。
羊城晚报:这次做《青蛇》,您说最大的感悟是就像经历了一场大的恋爱,能说《青蛇》是您戏剧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吗?
田沁鑫:我觉得创作并不是非要有对立或划分,或是强行规定什么。我的戏剧像一条河流,可能有的地方窄一点,有的地方宽阔一点,有的地方汇入大海,有的地方可能在树木和山崖间停滞。《青蛇》可能是我戏剧生涯这13年里,难度最大的一出戏。往常做的戏都是人的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关于人。《青蛇》是人、佛、妖三界,而且要打通这三界,所以比较难。
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也有一部分妖性,但大部分时间是人性。佛性体现在法海身上,他通过修行想成为佛。妖性体现在青白二蛇,她们在模仿人的过程中捉襟见肘,要面对来自人类社会的歧视和诋毁。她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以身体碰撞社会的,有时会出现很不符合常规的行为。即便白蛇想做一个良家女性,人生计划是在结婚后相夫教子、百姓人家、其乐融融、承欢膝下,但她真正的人生和计划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个走进婚姻的女孩都不会想着为离婚而结婚,而是怀着美好的图景才和那位走进婚姻殿堂。但结婚后可能会发现分歧,比如性格的问题,比如情感伤害,比如出轨,比如怀疑、颠倒梦想、恐怖、无情等,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婚前的那些想法。白蛇结婚之后,她身上的妖性在所有东西落空之下腾空一怒而起,嗔心大动使她淹了一座寺庙,成为临安城里最大的新闻。这也是良家女子做得出来的,她身上有这种妖性,而妖性也是我们人身上共有的。
人性是许仙这样的,大多数人是纯物质世界的,通过眼睛认识世界,看到什么事件具体解决,处处要有回报。没有更多的人生追求,只是想找个人结婚、生孩子,有的混得也不错,从小白领混成CEO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数十寒暑过了,人生就交代了。物质世界之外,能不能用精神来体悟我们的人生?大多数人不想,我们只要俗世成就,只要俗世的安逸。
羊城晚报:做完这出戏后您有什么改变?
田沁鑫:有两个变化:一是我的性别意识有些复萌。以前我对性别的感觉比较模糊,前几年我才感悟到我的灵魂应该是个种菜浇水的和尚,所以才解释了为什么我小时候不喜欢穿裙子,不喜欢首饰,不喜欢化妆。如果从俗世层面看,这个女孩有点像男孩,但我又没有在装扮和气质上很男孩那种,只是比较中性一点。我解释不通为什么会这样。排《青蛇》让我开始觉得,“哎,我是个女的呀”。因为小青很多东西是女的,有时我会做些示范,演员会说你做得很好嘛,很女人,然后我发现自己性别意识有些复萌,挺开心的。作为女性导演,有些女性视角和阐述,这样挺好的。但同时,我又想忘记这事儿,忘记这事儿我会更加自然,按照我的心情走。
还有一点变化是,做《青蛇》前我很想出家修行,想放弃俗世层面,但做完《青蛇》后,没想到这么多观众喜欢,我有点变了。比如一个星期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有些女性朋友看了两三遍还不断讨论,写微博博客的也那么多,我忽然觉得戏剧是个很好的“道场”。我们只要不让观众赔出时间和金钱来看一场空的戏,或是看一场让人觉得别扭的戏,只要我们和观众是朋友的关系,观看者和舞台表演者之间也是和谐的,可以共通探讨的,我觉得就很开心。我做这个戏后反而有一点入世,现在还舍不得戏剧,可能还会再做几出戏。
羊城晚报:您说青蛇要的是纯粹的爱,她不要社会规范。而生为女人的我们,无法做到她那么彻底。青蛇不仅仅具有爱的力量,她身上也有一种反抗性?
田沁鑫:青蛇是我尊敬的一种女性,她更像女孩结婚前,可能比较反叛、顽劣、愤怒、勇敢,不按父母的意志做事,寻找自己喜欢的男孩和想要的爱情。但往往大多数女孩会走向婚姻,相夫教子。但青蛇的坚持比一般女孩更彻底,她没有走向任何婚姻,她不想做她姐姐那样的良家女子,也不想按照人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她一直坚持她自己。她走得非常彻底,但人类社会给她的摧残和诋毁就更猛烈。
谈话剧生态
没有“怀才不遇”这件事
&不知道何时就会悄然而起
羊城晚报:您认为目前话剧的生存环境如何?
田沁鑫:中国目前还是在强势催生让戏剧变得活跃,原来只是一线城市,现在二、三线城市看话剧也都比较普及。各地的演出商、票务公司应运而生,大家都在接戏。我觉得戏剧和电影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戏剧会悄然而起。
以前我们都说广州是著名的滑铁卢,一出戏好像在哪演都行,但在广州就没人看。但近几年广州也在预热,话剧市场在慢慢好转,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在戏剧这个强势催生发展的时期,谁都逃脱不了,导演有时不愿意做一些牺牲也要做。可能那个戏排的质量很差,演出的剧场完全不对,是不是就不演了?原来从我个人固守的角度说,不愿意演,我认为戏剧是演给知音看的,但从普及戏剧以及满足更多需求的角度来讲,这种牺牲似乎是必须的,那我会愿意牺牲点个人名声。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艺术价值和商业的关系?一谈到在剧里做广告植入,人们就觉得是导演在向商业妥协云云,您是怎么看的?
田沁鑫:我做戏不考虑商业,也不大关心票房,只负责艺术品质,和我合作10余年的搭档、国家话剧院的制作总监李东,负责销售推广。你说的艺术价值和商业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有没有可能和他所处的时代同步表达的问题。如果从旧有的创作观念来讲,你可能会说,现在这个时代怎么变成这样了,有大量的商业元素,那艺术创作势必受到影响。但是换种思路,时代应运而生的,是属于年轻人甚至90后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导演不能吃老本,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很新兴的导演,和时代保持同步,不断获得能力上的增长。
羊城晚报:3年前,您和戴锦华老师有过一个对谈,谈到体制内外,谈到国家应该扶持艺术,尤其是戏剧。戴老师说,“没有艺术家想做贫困戏剧,但是经常是贫困时候做的戏,其饱满和震撼超过后来奢华的戏。”
田沁鑫:从我个人举例,做戏剧完全是出于热爱,是从体制外做起的。1997年我很想做一个戏,拉来朋友投资,中间有很多碰壁,但最终成功了。我先打预算,保证投资方的利益,尽可能让他们不赔本,也尽可能地联系剧场。由于第一次做没经验,所以没有演太多场,没让投资方赔本,其实如果我们当时继续演下去就赚钱了。首先我不是为了赚钱,但这点我现在跟朋友们说可能都说不通,大家会说不赚钱干什么?我觉得出于热爱,不赚钱又怎么了?只要你的热爱是精诚所至的,那么天道酬勤,一定会赚钱。所以付出是绝对的真理,索取不是。
还有一点,事情做不好是个人的原因,没什么值得同情。我觉得没有怀才不遇这件事,要不就是中途有很多困难你没有克服,半途而废;要不就是你智商不够高,没能力;再或者是你性格的问题,没办法达到“人和”。种种原因的失败并可以将“怀才不遇”当做理由,如果觉得做得很困难的话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谈戏剧形式
以蓬勃的生命力区别于电子产品
&活人的魅力弥足珍贵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
田沁鑫:戏剧是活人的表演艺术,这是戏剧的特质,和电影是有区别的。观众在电影院里先看到的是一个屏幕,电影结束后看到的还是一片空白的布,是一场空。而戏剧不是这样,观众进到一个黑屋子,靠灯光来构成舞台气氛。当场灯黑了,场铃响起,灯光把舞台打亮,你可以看到一个假想的社会,可以看到全景式的表演,就像全景电影一样,靠观众的眼睛来分镜头,但看不到具体的细节,只能看到舞台上的活人,以此构成很私密的故事。远处观众其实看不到演员的脸部表情,但为什么叫话剧,因为他会被演员的声音和讲述的故事所吸引,他会听到很多内心独白。
戏剧通过活人的表演艺术来传递内心的隐秘,尤其当他们在诉说心灵秘密的时候,观众会很幸福,观众会觉得只有我能看到他,是一个活人在跟我讲他心里的秘密。这和影像完全被动的吸收是不一样的,它有气息,台上人的一颦一蹙都会给下面的观众带来感动。比如你买张票走进戏院去看陈道明的《喜剧的忧伤》,那是真的看到陈道明在舞台上演出,在一刹那你会觉得跟他很近很近。包括我做《风华绝代》,很多人想看刘晓庆,无论一线城市还是各种地级市,场场爆满。当她本人用三个小时给你尽情演绎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她从脸到胸到腰到腿全景式地在舞台上给你表演,那个震撼是不一样的。
戏剧的艺术质感能够带给观众人与人直接的信息交流,因此舞台剧艺术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不但不会消磨,反而会以蓬勃的生命力来和电子产品区别开来。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肯定会去看舞台剧,因为这和我的电脑、电视太不一样了,活人的魅力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来源:羊城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