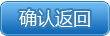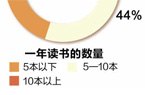美国华侨陈光锦寄给家人的银信(银信封正面,1919年)。詹雨鑫翻拍

现存最早的潮汕侨批。林旭娜 摄

新加坡致成批局1909年3月25日收寄的批信。林旭娜翻拍

19日,在韩国光州市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上,“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申遗成功的消息一经传来,海内外华人倍感振奋。
“侨批档案”是广东诞生的首项世界记忆遗产,它的成功“申遗”,标志着在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记忆遗产四大类世界遗产上,广东已实现“大满贯”。
在学者眼中,侨批档案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国际汉学家饶宗颐盛赞侨批为“侨史敦煌”、“海邦剩馥”,而在海外华人华侨的眼中,侨批是移民家族史和情感纽带的不朽见证。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侨批申遗6年来,一直牵系着海内外华人的心。
构成本次申遗“侨批档案”的约17万份侨批中,来自广东的达到16万件,占中国内地已发现侨批总数的80%以上。申遗成功之后,侨批档案的进一步收集、研究、保护,引发社会关注。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詹雨鑫
实习记者 潘伟珊
策划:孙爱群 郎国华
统筹:金强
“草根”档案独一无二
■遗产价值
侨批档案的收发双方和运送中介,是一个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广泛人群,他们留下的丰富档案,并不仅属于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家族,更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世界
侨批申遗成功牵动人心,然而,普通读者也许会问:出自100多年前出洋“草根”之手的书信和汇款凭证,为何能成为全人类的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的主体都是“小人物”,其价值为何让众多大家拍案惊奇?
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埃德蒙森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此给出了权威的答案:侨批档案的收发双方和运送中介,是一个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广泛人群,尤其是催生这一特殊现象的中国早期国际移民,还承载了东西方多层面的交流,甚至持续了数个世纪。埃德蒙森认为他们留下的丰富档案,并不仅属于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家族,更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世界。
而早在十几年前,国学大师饶宗颐就指出,作为民间原生态“草根”档案文献,在时间上,侨批和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可以形成自然链接,系统反映社会演进;在空间上,又覆盖了华侨海外活动区域及侨乡各县,影响面广。
这些侨批发源、流传于民间,收藏于民间,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记载翔实,内容丰富,因为横跨几大洲,侨批档案涉及到世界交通史;大量的国际移民,涉及国际关系乃至军事领域;创造性地设立侨批局,涉及国际金融业;侨批往返涉及跨国邮政。所以,侨批档案是研究近代华侨史、家族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等的珍贵档案文献。
而侨批内容更是包罗万象,大到“世情”、“国情”,小到“乡情”、“亲情”,成为最好的社会“切片”和标本。
广东省档案局编撰的《海邦剩馥——广东侨批档案》一书中就有很好的例子。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濒临破产,通货膨胀急剧发展,物价飞涨,华侨寄回批款的国币折合数额也不断飞升。1946下半年,一笔赡家批款的数额通常是国币5万元,到1947年上半年是国币20万元,下半年变成国币80万元左右。1948年起,批款的交寄金额逐月急剧上升,从每笔100多万元国币上升到数千万元,到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改用金圆券代替国币前夕,一笔赡家批款竟飙升至近亿元国币,但已形同废纸。
泰国集邮家、收藏家许茂春曾经捐赠给潮汕侨批文物馆一批侨批原件,其中一个于1949年5月5日从汕头寄出的总包封,仅装10封回批,邮资竟高达525万元,信封背面贴了50枚面值为10万元的邮票仍不够邮资,还在信封的正面补贴7枚邮票,成为货币贬值的活见证。这些生动的原始材料,是研究当时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最好的文献。
对此,五邑大学校长张国雄分析,侨批档案并非简单的华侨家庭书信,而是广东侨乡150多年历史中与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各国和地区发生广泛联系的文献见证,是人类的集体记忆遗产。
“侨批来源于民间、运转于民间、收藏于民间,其草根性使其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起到较好的佐证和补充作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王炜中认为,华侨与家眷简短、朴素的往来书信中,透露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它是跨区域、跨种族、跨文明的交流。
侨批还具有审美价值。记者从申遗报告文本中看到这样的描述:“侨批档案代表了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书信形式和风格,集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篆刻艺术于一体,具有杰出的审美价值。从书写形式的起笔称谓、问候,到内容的用语习惯和思维方式,再到结束的方式和礼仪用词等等,浓重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习俗文化和语言价值……”在传统书信被手机、网络替代的当下,这16万封侨批得以保留,弥足珍贵。
海内外华人热切关注
■申遗过程
侨批申遗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热心侨胞或是重金收集侨批,或是捐出自己珍藏的侨批,或是专门去信国家档案局反映海内外对侨批档案申遗的强烈愿望,为侨批申遗鼓与呼
不久前在泰国参加五邑银信的展览时,泰国华侨对侨批的感情给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刘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有一个说法,‘侨批是华侨悲情史的见证’,一些老华侨一边看着侨批,一边掉眼泪。”刘进说,看侨批,就像看一部闽粤先侨史。
在泰国,一位77岁的老人与侨批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他就是许茂春。
祖籍广东澄海隆都镇的许茂春是泰国中华会馆主席,30多年来收集侨批近3万封,覆盖潮汕、客家、福建等区域。为了延续侨批档案中的集体记忆,让子孙铭记这段历史,他重金收集侨批,用实际行动支持申遗。
王炜中告诉记者,许茂春曾为了十几封侨批,不惜花20余万美元从别人手里购下整部《荷属东印度群岛实寄封》邮集。他也曾花费33万元拍下一个中国解放时的侨批回批总包封,而这样的经历还有好几次。
2008年,许茂春分类整理了自己的藏品,出版《东南亚华人与侨批》,对侨批的总结和推介具有很高价值。只要是涉及侨批的研讨会,他总是抽出时间到场。侨批档案申遗工程启动后,许茂春继续到处奔波,出钱出力。
这样的热心侨胞还有很多。王炜中回忆,2004年,时任新加坡议员的成汉通先生一家回家乡潮安县龙湖镇银湖村祭祖探亲,没想到从祖屋阁楼找到了一个藤篮,里面有很多侨批。当成汉通看到潮汕侨批文物馆馆藏丰厚,已藏有10万余封侨批,并整理得很好时,立刻提出要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侨批捐赠出来。
“成汉通先生捐赠的60多封侨批最新的也有50多年历史,十分珍贵。而新加坡正是目前确切证实的最早潮帮侨批局致成批局的诞生地。”王炜中介绍,到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民信局。
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虽已年过九旬,也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侨批档案,自申遗之日起,老人家一直关心申遗进度。他曾说过,徽州留下有特殊价值的契据、契约,而潮州可与之媲美的是侨批,这种价值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饶宗颐曾为潮汕侨批文物馆多次题词,有“海邦剩馥”、“媲美徽学”等(如左图)。
全国侨联原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的祖父庄书良先生曾主营侨批业,他的儿子中有4个继承父业,堪称侨批世家。庄世平多年力倡侨批文化研究,并亲自为潮汕侨批文物馆命名。
为促进申遗工作,年已九旬的香港爱国实业家陈伟南先生和有关人士专门去信国家档案局,反映海内外社团对侨批档案申遗的强烈愿望。海外多家华文报刊也一直跟踪报道侨批档案申报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进度的消息。
期待民间参与保护
■保护研究
政府需加大对侨批档案遗产的持续投入,还需要提高全民对记忆遗产的认识和对侨批保护的意识。侨批的研究必须从多学科的研究、跨国的研究以及国际移民书信比较研究多种角度开展
作为文书档案,侨批相比广东的其他几项“世遗”冷清得多,自然遗产丹霞山,文化遗产开平碉楼,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广东剪纸早在申遗成功之前,因同时具有显而易见的观赏性和文娱性更易受大众关注,也更容易实现经济转化。
但侨批档案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学术界和民间双重冷漠对待,只有少数收藏家慧眼识珠。
随着侨批申遗的步步推进,学术界对其关注度略有提高。几年来,已有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加入到侨批的研究中,申遗成功无疑将吸引更多顶级专家参与到这一跨地域、跨学科的珍贵档案的研究中。
相比科研,民间的关注和介入也是有识之士关注的重点。汕头市金荷中学教师曾组织学生成立研究兴趣小组,连续3年组织学习和研究,并在第二届侨批文化研讨会上推出《金荷中学侨批小论文集》,让与会专家刮目相看,然而,随着该老师的调动,兴趣小组能否继续保持活力,让王炜中感到担忧。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接连两周在收藏五邑侨批的主要场所——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外围广场发放200份关于侨批知悉情况的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89份。调查结果显示,了解“何为侨批”的只有18人,约占9.5%;而对于是否知悉侨批正申报成为世界遗产的提问,93%的人表示“不知道”。侨批档案现已列入世界记忆档案,但在它的“故乡”却被人们以“一脸茫然”回应,令人不胜唏嘘。
此前,记者走访江门市档案局,在其《五邑银信档案图片展登记表》上看到,登记进场参观侨批展览的多是高校因课程需要,组织学生前往参观的,其余便是若干学者的名字。笔者询问参观侨批的学生,大多数表示看过后“没啥印象”。
张国雄认为,由于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相距较远,国内大部分人对世界记忆遗产的认识仍较薄弱。据他介绍,早在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时已大量地使用了侨批档案,这也是申遗成功的一个重要支撑材料。
他告诉记者,当务之急应是针对申遗中遇到的难点,逐个攻破。最基础、最迫切的是,政府需加大对侨批档案遗产的持续投入。其次,是提高全民对记忆遗产的认识和对侨批保护的意识,希望民间有更多力量投入进来,共同参与保护。"
王炜中也认为,申遗成功并非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因为还有大量后续工作。“现在还有很多散落在民间的侨批等待我们去收集,把它抢救出来,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
除了保护,还需研究。王炜中认为,侨批的内涵非常丰富,“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目前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侨批的研究必须从多学科的研究、跨国的研究以及国际移民书信比较研究多种角度开展,整合社会上各个学科学者的研究力量一起开发。
王炜中还建议,在后续的侨批研究中,要注意提炼侨批精神,升华侨批文化,将之与现在的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同时,要注重传播,尤其是向下一代的传播,通过发扬、实践侨批中蕴含的精神,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不能忽视侨批民间保护的爱与伤
◆记者手记◆
张国雄告诉记者,侨批属于民间私人信件,分散于广大乡村,而且由于是纸质文献,容易因潮湿发生霉变,或被虫蛀蚀,很多家庭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条件将之作为档案文献进行保护,因而,侨批的档案保管任务十分繁重,申遗成功后,需要抢救的侨批数量巨大,而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还远远不够。
侨批申遗的六七年,也是它逐渐主流化的过程,很多民间的集邮爱好者也加入到这股潮流中。
很多研究者一直企盼民间力量参与到侨批的收集和保护中,然而,民间的参与是否有利于侨批档案还需要具体分析。如五邑地区民间侨批收藏家罗达全就认为,近年收藏界逐渐掀起“侨批收藏热”,普通的五邑侨批,原本10多元即可买到,但这两年一封近乎卖出100—200元,拍卖会上有的甚至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据其所述,部分民间收藏家对侨批认识不足,在其买回侨批后,又将之高价卖出,经过不同的人多次倒卖,或对侨批的整体研究造成影响。
此外,虽然广东地区的侨批已经整理出版了部分书籍,但书籍中主要对侨批主件进行展示,侨批档案的附件仍极少被认识,且侨批的研究尚未进入专业学者的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力量仍十分薄弱,多方因素共同导致了申遗成功后的保护之“难”。
侨批业的特殊运作
初抵异地,移民们无暇多顾,迅速全力投入各种营生。通过一段时期的辛勤劳作,节衣缩食,逐渐有了些积蓄。然而,当时的大清国与侨居国尚未通邮,也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海外游子与家乡亲友联系的心愿难以实现。
随着海外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递送银两、家书的需求日益强烈。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委托回国的亲友和同乡捎带银信。最终,在金融邮讯机构尚未正式建立或极不完善的年代,银信合一的特殊寄汇方式——侨批应运而生。一封薄批,几句嘱言,再加上若干辛苦钱,为家乡亲人送上异国游子的拳拳关爱。
水客递送时期
侨批诞生之前,已经出现了为海外华侨递带“人、信、财、物”的特殊人群,就是原始的水客。随着近代交通、金融业的发展,这些水客由原来递带“人、信、财、物”并重,逐渐转变成主要为海外华侨递送“银信合一”的侨批。于是,水客业日渐兴旺,成为侨批传递的重要形式之一。水客一般凭个人信用经营业务,常为父传子、兄传弟的家族事业,通常按寄款额3%-5%的比例向寄款人收取手续费。19世纪到20世纪初,水客业渐兴盛,20世纪30年代,每年经水客带回款项达国币2000万元,占全国汇款5.2%。
批局承办时期
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侨批递送需要,19世纪30年代左右,以批局、银号、商号等承办机构为代表的侨批业正式出现并迅速发展,受到华侨及侨眷的普遍欢迎。虽然侨批业与水客业还同时并存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批局承办逐渐发展为侨批业的主流,在潮汕及南洋尤为盛行。据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商业》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达541家。侨批业兴盛时期,潮汕地区侨汇80%以批款形式通过侨批局汇入。
银行统管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对侨批业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鼓励拓展民间侨汇业务。其实,侨批业作为争取外汇的主要渠道,深受中央重视。随着国家银行侨汇业务的不断发展,侨批业的性质也发生变化,转变成为国家银行吸引外汇的一种代理机构。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明确要求“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业务统归为中国银行专门办理,至此,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来源:南方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