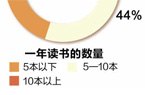◆阮鉴祥
提起《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时下的年轻人也许闻所未闻,但在经历过“文革”那代人的印象中,却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的轰然而起,就是从批判这套书为象征的,而我恰恰收藏着这套刊印于“文革”前的书籍。
“文革”的“青蘋之末”,肇始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点名批判的是著名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由于批的是一出京剧,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到了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出笼,政治空气完全不同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从天而降,直接点名批判的对象也从吴晗扩大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和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并导致其中两人即邓拓和吴晗遭迫害含恨而死,而廖沫沙虽幸免于难,但也遍体鳞伤,饱受摧残。
姚文元对邓拓(马南邨)撰写的《燕山夜话》和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之名合著的《三家村札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诬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当时书中是怎样写的,大家都没有看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竟让我得到了这套书。由于我爱写写弄弄,经一位同学介绍,被推荐到一个群众组织办的刊物《新上海通讯》当编辑,并定期到当时已停刊的《新民晚报》社印刷,一来二去,和报社印刷车间的工人师傅都混熟了。一次,不知怎么提起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套“大毒草”,当我说起从未看到过该书时,一位相处较好的老师傅悄悄地把我拉到角落,说他有这套书,如我实在想看,可以送给我。我自然喜出望外,连连称谢。
于是,在不到一个月里,我偷偷地读完了这套书,只觉得书中充满了知识和智慧,看不出毒在哪里,当然也不敢和别人说。1968年我去云南当兵,就把这套书藏在阁楼上,以后也就忘了。没想到日前老宅装修,这套书又被找了出来,欣喜之余,我除了重新阅读一遍外,还对书的取名、装桢和印刷等进行了研究和观察。其中《燕山夜话》中的“燕山”喻指北京,“夜话”是因这个专栏开辟在《北京晚报》副刊上,为工作之余所读的“闲书”。此书32开本,共五册,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新华印刷厂印刷,第一册第1版于1961年8月印刷,印量为20000册,单价为0.26元。第二册到第五册分别印刷于1962年2月至1962年12月,印量从20000册增至70000册,可见受读者欢迎而畅销,单价则从0.29元上升至0.35元。书的封面分别为浅绿色和深绿色。《三家村札记》的“三家村”或许得名于陆游的《村饮示邻曲》一诗中的“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之句,为8开本,出版于1966年4月。该书没有标售价,疑为内部发行。现在,尽管《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连同他们的作者早就得到了平反,但如今在书店很难见到它们的新版。如此,我这套刊印于“文革”前的书籍就十分珍贵并很值得收藏了。
(来源:新民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