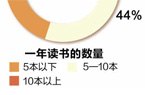柯麟院长与参加全国妇产科学会代表在一起。

柯麟在学生留言本上留言。
■核心提示
柯麟根据自己人生和工作的丰富经验,在教学上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一方面,他认为既要吸收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又要按中国国情办教育,在教学改革中,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为医学生除了掌握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参加实习。同时,他认为在学术上不应当“肯定一切”,也不应“否定一切”。应该要讨论研究,取长补短,走出自己办学和医疗事业的道路。
几十年来,柯麟坚持实事求是,按照高等教育固有规律办学,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他以非凡才智驾驭中山医学院这艘巨轮,抗击惊涛骇浪,进入“潮平两岸阔”的发展阶段,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
他审时度势,巧化矛盾,立“三基”、“三严”学风至今仍被奉为圭臬;他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殷殷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团结广大师生员工;极力为教师科研创造良好条件,引领中山医建成全国重点医科大学;改革开放后,柯麟以80高龄重回中山医并参与创办暨南大学医学院,书写我国医学教育新篇。
柯麟的学生、老下属卓大宏教授在著作《红楼情愫,青山感怀》中向老院长献词:“医教师表兮,百代之所宗;雄勋伟业兮,后世之所崇。”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对话《柯麟传》作者之一、中山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康复医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卓大宏教授,回顾柯麟的30年医学教育路。
在广东省档案馆,有一组有关柯麟工作安排的来往信件。1950年10月29日,叶剑英和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写信给中央:因中央医院中山大学医院及医学院在华南起领导作用,现无适当人选,拟任柯麟医生为上述医院及医学院的院长。还可兼顾澳门方面的工作。周恩来总理在11月7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卫生部要求速调柯麟来京任办公厅主任。新中国刚刚组建,人才奇缺,柯麟成为京粤两地都想调动的对象。但心思缜密的周恩来提出了第三种方案,柯麟如尚需留澳门,则两处均可不调。
经再三斟酌,柯麟于11月14日复电周恩来总理,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决定,回广东工作,这样可以兼顾澳门的工作。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意见。
1951年春天,柯麟离开生活了15年的澳门,举家迁回阔别20多年的广州,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并兼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此后,他多次带着中山医的教授到澳门讲学、交流。
根据国家关于院系调整的方针,在柯麟的组织和带领下,1953至1954年,中山大学医学院与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实现了三校合并,合称华南医学院。1956年至1957年间,他还作为团长,率中国医学代表团先后访问日本、印度和巴基斯坦。
巧化门户之见 力促三校合并
南方日报:柯麟和中山大学医学院有三段不解之缘。
卓大宏:是的。柯麟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正式调令后,在1951年春节全家迁到广州。他本来在中大医学院读书,是广东公医学校仅有的5名公费生之一,和阔别26年之久的母校有着很深的缘分,在1926年毕业后,还曾留校附属医院从医。直到文革后,柯麟老院长又重返中山医学院,他的一生与中山医结下三段不解之缘。
一执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山医,柯麟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澳门朋友报答他的酬劳费共15万元交给组织,一半作为党费,一半资助学院建设。他还动员澳门镜湖医院的一些医护骨干到中山大学医学院工作。
南方日报:在任上柯麟做了一件大事,就是三校合并,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卓大宏:1952年,中央决定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当时全国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生仅有几万名,两广地区才两三千名。而广州的三间医学院总的说来,力量比较薄弱和分散。柯麟认为要把力量集中起来才能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因此主张把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三所医学院合并起来。广东省和中央的有关部门同意了这个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53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作出了先将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岭南大学医学院两院进行合并,定名为华南医学院的决定,再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两个学院的全面合并工作完成,8月12日,华南医学院正式成立。之后,又在第二年8月把光华医学院合并过来。
南方日报:在此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卓大宏:华南医学院成立前后,原来三所医学院的学术传统各不相同,这是摆在柯麟面前最大的难题。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称作“德日派”,岭南大学医学院则奉“英美派”,它们都是长期在旧社会的政治背景影响下办的旧大学,历史传统各异,教师来源和学术派别也有很大差别,办学各有特点,门户之见比较深。
为此,柯麟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多次座谈会,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认为要办好大学,校领导应经常听取教授们的意见,他常说:“办大学不依靠知识分子依靠谁?特别要依靠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十分强调以“和”为贵,为了医疗发展的共同目标,要努力搞好团结,和衷共济。在敏感的人事安排上,他也是慎重协商,注意一视同仁,因材使用,不断物色和推荐优秀的知识分子担任学院的领导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三间学院的师生逐渐消除了隔阂,尤其是教授们开始相互合作,积极发挥作用。当时的华南医学院还集中了不少医学教育界的精英。其中一级教授就有病理学家梁伯强、秦光煜,放射学家谢志光,眼科学家陈耀真,寄生虫学家陈心陶,内科学家周寿恺,生理学家林树模,儿科学家钟世藩等八人,还有陈国桢、罗潜、毛文书、白施恩、汤泽光、邝公道、王成恩、叶鹿鸣、许天禄、龚兰真、许鹏程、林剑鹏等一批著名专家、教授,他们都被安排担任了行政、教学、科研、医疗等各方面的重要职务。柯麟还推荐罗潜教授(解放前曾任过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桢教授(原岭南医学院副教务长和内科主任)分任正副教务长,推荐他的老战友王季甫担任总务长。在后来成立的院务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1961年,柯麟还亲赴香港接回港大医学院的著名病理学家侯宝璋教授,并陪同他在内地参观考察。不久,侯教授举家定居北京,出任中国医大副校长。
南方日报:听说,在合校前后,有些来自不同学校的教授对柯麟不大了解,对他领导高等医学教育的能力和经验曾有过一些疑虑,后来是怎么消除的?
卓大宏:柯麟院长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对政策的稳健把握以及远见和气魄,特别是他十分尊重和团结一批名教授,礼贤下士,问治校之道于名师,常常听取各位教授学者的意见,积极从名教授处汲取经验。因此,学校的各项工作进步也很快,成绩很大,师生员工对柯麟院长的治校努力和贡献都很佩服和敬重。
勇立“三基”、“三严” 筹建专科医院
南方日报:柯麟院长十分注重教学质量,当今中山医学子无人不晓的“三基”、“三严”学风,就是他提出的。这学风,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卓大宏: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整治运动比较多,师生下乡下基层较多,使教学秩序受到冲击。柯麟始终认为,医学院学生要学好科学知识才能担负救死扶伤的重任,他还说医学生不能做空头政治家,要维护中山医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影响学生的学业。所以,他提出了1:2:9的制度,即学生在一年中,有1个月放假,2个月下乡下厂劳动,9个月在校学习,还提出下乡下厂不仅是参加生产劳动,也要结合卫生医疗工作和卫生运动的实践,把这一经历视为专业的学习和锻炼。上世纪60年代初期,高校强调整顿、提高,柯麟集中了一批富有治学和办校经验的老教授的智慧,强调学生的学习要打好基础,学校医教研工作要有研究的要求,经过这一系列工作铺垫,中山医形成了著名的“三基”、“三严”学风——就是“注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在教学医疗和科研中,坚持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严格的要求”。此后,学校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有了飞跃发展。比如,继1963年上海陈中伟教授创造断手再植的世界第一例;1964年,中山医年轻教授黄承达,也创造了断脚再植的先例。
1964年1月,卫生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医学教育工作会议,柯麟院长作为发言代表还向董必武、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介绍“三基”、“三严”的经验,受到了满堂的赞誉。
南方日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号召“向苏联学习”。1953年,柯麟院长和梁伯强教授访问了苏联。在教学方法上,柯麟院长对苏联经验持怎样的态度?
卓大宏:柯麟根据自己人生和工作的丰富经验,在教学上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上,他是积极的,但他并不主张完全照搬苏联。一方面,他认为既要吸收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又要按中国国情办教育,在教学改革中,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为医学生除了掌握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参加实习。但是当时学院学生多,附属医院病床少,一共还不到500张,临床和生产实习都僧多粥少,困难不小。为解决教学实习病床不足的问题,柯麟向省、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支持建立广州医教卫生技术资源大协作,中山医同其他10所医院建立教学合作关系。它们给学院提供了2000多张病床供临床实习。之后,广东省各地的20多所医院都被纳入了实习的定点单位。这样,不但扩大了学生实习基地,而且实习的学生也得到更多医疗专家的指导。同时,他认为在学术上不应当“肯定一切”,也不应“否定一切”。应该要讨论研究,取长补短,走出自己办学和医疗事业的道路。作为炎黄子孙,要批判继承中国的医学遗产。
南方日报:在当时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学校发展很不容易,但中山医却独树一帜,这和柯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无关系。他是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的?
卓大宏:之前我说了,合校后中山医有“八大教授”等鼎鼎大名的医学专家。柯麟一直尽力向上级申请,给教授们尽可能提供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例如在肿瘤学科发展方面,1956年,经柯麟向省委申请批准后,附属医院设立了肿瘤专科门诊。到了1958年又成立了谢志光教授领导的肿瘤科。1962年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三十三篇学术论文中,就有三篇是中山医提交的,相当有影响力。1964年,中山医建成附属华南肿瘤医院,为一批肿瘤临床和研究专家提供了优异的工作条件。
同时,柯麟对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的支持力度也很大。陈教授是眼科学的“活字典”,他被柯麟推荐担任中山医第一任的眼科教研组主任,还配备了助手,安排了研究实验室。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六年制高等医学院校的《眼科学》教材。此外,柯麟还全力支持他与夫人毛文书教授关于在华南建立第一间大型眼科医院的建议。经过上下奔跑和多方努力,1965年建成了中山医学院附属眼科医院,这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医科高等院校附属眼科医院。
柯麟还经常到陈心陶、陈耀真、秦光煜、钟世藩、林树模、周寿恺等的课堂去听他们讲课。许天禄的课堂教学技巧高明,被誉为精于“形象教学”的教授,叶鹿鸣的大体解剖技术精湛,人称“一把好刀”……对这些,柯麟都大力赞赏和推广。
文革被斗不记恨 80高龄重返中山医
南方日报:您在《红楼情愫,青山感怀》里这么评价柯麟院长:“培育专才,桃李盈门,含笑天使”。在您看来,柯麟院长是怎么对待学生的?
卓大宏:作为一院之长,柯麟心里始终装着他的学生。柯麟主持医学院工作以来,一直以德、智、体三方面来要求学生,争取把他们培养成为既有好的医术,又有好的医德,身体健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者。他十分重视用革命传统来教育学生。他经常向学生们讲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中大医科的爱国学生运动史,同团干部讲,在学生集会上讲,在学生会干部访问他时讲,在同学生闲谈时也讲。
此外,为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柯麟专门定期和几位学生干部座谈了解学生的情况。很荣幸我当时是学校共青团干部的一分子,所以和他有比较频繁的接触。他总是询问我身边的同学生活过得怎样,吃得好不好,还亲自到学生宿舍、食堂、球场看看学生们过得怎样。当知道女生洗澡房水力不足,柯麟便指示修理部加装水箱,一定要解决学生洗澡难问题。有这样一位真切关爱学生的院长,同学们自然尊敬、爱戴。所以对我们这一辈来说,他就像个慈父。
南方日报:在文革时期,柯麟也曾遭到学生批斗,后来,他为何又重返中山医?
卓大宏:那是出于他对中山医的感情。“文革”十年,中山医受到干扰,柯麟遭政治迫害。1980年5月,他又被任命兼任中山医学院院长职务。这时柯麟已近80高龄。他回到中山医,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欢迎。但“文革”初期,也就是1966年,柯麟是大字报批斗的对象。当年,一个因为四门课程连续补考不及格、按规定给予退学处理的学生,和一个因为患病半年、功课赶不上而被留级的学生,先后张贴大字报,攻击柯麟“打击、排斥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造反派”在1966年文革大乱中,当柯麟一回到广州就立即把他押送回学院,送到“牛鬼蛇神管教队”审查。
但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文革”大乱,柯麟遭到自己学生的批斗,那种苦只有自己啃。打倒“四人帮”之后得以拨乱反正,回到学院后,柯麟就与曾经批斗他的学生开会。在开会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记恨,反倒对学生所作所为作出谅解,还鼓励他们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中好好学习。他说:“当前的任务应当是总结这次浩劫的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蹈覆辙,共同向前看,不应该纠缠算旧账,计较个人恩怨得失。”1984年后因年事已高,柯麟不再担任学院的领导职务。当听到邓小平为改名后的中山医科大学题写校名,邓颖超为校门口的孙中山青年铜像题词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南方日报:后来您也当了学院的领导。在您看来,柯麟院长的精神和事迹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和哪些宝贵经验?
卓大宏:首先,我很敬佩他的为人。举个例子,柯麟从澳门回穗后带回了4部小车,除1部留在中山医留作公用外,其他全部上交给了组织。至诚至忠,恪守党员原则,不用公家一分一毫,柯麟就是这样的人。我还曾在“纪念柯麟院长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上表达过我对柯麟院长教育思想的崇敬,其中影响我至深的是老校长的治校“三力”——稳健的领航力,高度的凝聚力,强烈的感染力:在教改风浪中排除干扰,历次运动中实事求是,按教育规律的大方向导航,这是领航力;他本人之人格魅力及人生经验,得以凝聚五湖四海之士齐心建校,这是凝聚力;身教言传,维护师道尊严,关爱青年学子,鼓舞师生员工,团结一致,这是感染力。有这“三力”推动,才有中山医今天的成绩,这让我终身学习,受用终身。
(感谢卓大宏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素材,稿件经其审定)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实习生 何超 通讯员 李绍斌
(来源:南方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