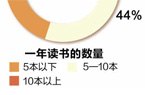2009年5月12日,李西闽重回当日被埋废墟。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林环 实习生 杜鹏燕
昨日凌晨1点半,李西闽从噩梦中惊醒。梦中情景,一晃,已过去了5年。
每年的这一天,他都会从上海的家中,飞往四川彭州银厂沟,去那片长满野草的废墟和死难者的坟茔,祭奠。
那是他2008年曾被活埋了整整76小时的地方。
那是这位以恐怖小说闻名的作家,有生以来最真实最恐怖的76小时。
没有人敢说他不是一条硬汉:钢筋从他身体穿过,铁片从他左脸插入,极渴时却由于被牢牢压住而无法喝到自己的尿,一次次即将昏迷时就一次次用手背往铁钉上使劲刮、一次次把头往下压让脸上的铁片插得更深更疼……竟这样,熬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成为山庄里同时被埋的好几人中,唯一幸存者。
然而,今年的5月12日,汶川地震的五周年,对他而言却有些特殊。
大半年前,他被确诊患了抑郁症和创伤综合症。家人实在忧心他重回受难地。
但他没有放弃。说服了家人,再一次去往那个——
他幻想,自己可以勇敢直面的,噩梦之地。
自杀
死神,就在近处,冷漠地睨视着他。
去年9月7日,李西闽自杀,吞了大半瓶安眠药。
他没有想到,慕容雪村、宁财神、陈村等多位好友会在微博上为他求救。
好友们的敏锐,源于他深夜在微博上写的两句话。一句是回复网友“@自由并理想”的:“如果今天晚上我离去,也许你会爱上我留在世上的文字。”还有一句是凌晨1点14分发布的:“我一直相信,在未来那个地方,我们都会在一起,那是个花园,我们相亲相爱,没有仇恨,没有忧伤,花香弥漫,爱欲横流……”
凌晨2点后,网上兴起寻找李西闽的热潮,并确认其方位在老家福建长汀。
他的电话一直在响,他置之不理,昏昏沉沉的,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打开房门,将他送入医院洗胃。
许多网友恶骂他炒作,甚至有媒体直指“网上所谓的自杀传闻是一场误会”。
对于“炒作说”,他并不在意。但他确感羞愧,只因,“对不起那些爱我的人”。
他在网上两度道歉——“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好好活着,只能保证以后不会再惊扰大家”!
活着,对他而言,太难了。
身体疼痛难愈,内心绝望积郁。
他总牢记,正月里,老家的一名堂弟打麻将时自摸糊了,大笑,然后倒地,心脏病发身亡,年仅20岁。
死亡,如此接近。
回沪后,惊魂未定的妻子带他去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抑郁症和创伤综合症。
从此,他每天服用的药物,超过了十种:止疼的,治骨伤的,抗抑郁的,助睡眠的……
只要两天不吃,就有明显的情绪变化:好几次,试图纵身跃下,从他35层的家中——
也就是,我对他的采访所在。
不禁,我们都看了看窗外,正是阴雨天,不见丝毫阳光。
灾难
阳光倾泻中,他把QQ的签名改成了“风自由地穿过山谷”。
那个2008年5月12日的午后,他断不会想到,在这样风景如诗的山庄里,在如此适合笔耕的幽静处,灾难瞬间即至。
突然,仿佛多列火车从地底驶过,天花板砸落,吊灯砸落,楼塌了。
血糊住了左眼,仅右眼可见,废墟中一条缝里的,一缕光。
是山体滑坡吗?或只是新建的度假山庄倒了?他听不见任何尖叫声、痛哭声,当然不知外头已是人间地狱。
“救救我!”他声嘶力竭地喊着。终于,有山庄的管理人员听见了,但来了几回,承诺救他,却又无力施救,走了几回。
他嚎叫一声,困兽般无奈而悲怆。
三天三夜。天暗了又亮,亮了又暗。
他渴极了。但被压得无法动弹,珍贵的尿喝不到,顺着楼板流下的雨水连嘴唇都打湿不到,就连想歪个头喝自己左脸上的血,也做不到……
救援界一般认为,72小时是人体缺水维持的极限,这个与死神赛跑的“黄金救援期”过后,生存靠的就是意志力。
他看见了一个光环,巨大的光环,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他的身体,仿佛飘起来了。
天堂、地狱的一线间,他挣扎着吼自己:“李西闽,你不能死!你从来都不是孬种!”
保持清醒,必须保持清醒!他想到了尚有知觉的右手,就将右手手背放在一块木板突出的铁钉上使劲地刮,一次次即将昏睡,一次次用力刮。
他还刻意地把头往下压,让插在左脸太阳穴附近的铁片,插得更深些,再深些,直到清晰听见血冒出来时咕咕的声响……
获救后,他才知道,“整个文学界都为李西闽牵着心肠”。从知道他被埋的消息起,“王干、朱大可、裘山山等作家们就都开始呼号奔走”,“可道路仍是阻断的,韩寒的营救小团队多次试图进入却未果”。友人感慨:“面对自然的劫难,文学派不上任何用场。”
获救后,他才知道,在什邡工作的好友易延端13日晚听山庄逃亡人说李西闽被埋,借车赶往,路遇一位姓席的志愿者主动帮忙,就同车冲过几乎全线垮塌的山道,在最后12公里时由于大石滚落、道路遇阻,而弃车趟河徒步。赶到山庄时,已是14日傍晚。二人用电缆拴住腰,头朝下脚朝天,钻进正在余震中晃动的水泥板下,用小铁锤和双手营救……最终,只挖出一个小洞,连水都送不进来……易延端大哭,天亮后,守候在公路边的他斗胆拦下一支空军部队。
曾在空军部队服役20年的李西闽,终被空军官兵用力拽出了废墟。
被背出山庄的那一刻,他回头一望,才发现,埋住他的废墟斜斜地挂在山谷边缘,摇摇欲坠。
而对面的半座大山,已经坍塌。
如今,这名素来被认作硬汉的老兵,居然变得恐惧乘地铁。
正是因为,在他听来,地铁启动时的隐约轰隆声,像极了将他越压越紧的一次次余震。
战争
但他的出行,大多只能依赖地铁了。
汶川地震五周年,他的骨伤难愈,至今左手都没有握力。给记者沏茶时,小小的茶杯,他左手拿起,竟会微抖。
所以,他再也不能开车了。
阴雨季节,疼;深夜醒来,疼。但身体上的疼痛,这种被友人形容为“钢筋和骨头咯咯摩擦的”疼痛,远比不上他抑郁症发作时的疼。这种疼,早在他被确诊患了抑郁症之前就已频频发作。
你以为抑郁症只是心里难过吗?不!
发作时,莫名其妙心悸、头疼,就是身体某个地方突然疼痛,疼得你简直受不了。李西闽说。
就连他6岁的女儿李小坏,在他心跳骤然加快、心像针扎一样痛时,都会为他拿药、倒水,摸摸他的心口,有时还会掉泪。
那心脏本身是健康的吗?记者很疑惑。
是,我检查过,没有心脏病。他平静回答。
是的,就是这样。
现在的他,除了文学圈那些朋友,多了一群特殊的朋友:抑郁症患者。他们有自己的网络聊天群。
群上有网友说,“得了抑郁症,就觉得没什么疼可比拟了”。他极为认同。但这确实是许许多多普通人所不了解的。
地震之后,他不记得已有多少次,在暗夜里从噩梦中惊醒。
恐惧深入骨髓。看到汽车,就不由地想到车祸;有点风吹草动,内心就瑟瑟发抖。尤其是独处之时。
再不像以前那样大咧咧、无所畏惧了。
这一点,许多普通人同样无法理解——你是地震中的幸存者,你比那么多人都幸运了,应该活得很好、珍惜生命才对。
是的,和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相比,我的确很幸运。可是,我的恐惧无法消除,我总在否定自己。李西闽说,如今他特别理解自杀的人,包括灾区那些自杀的幸存者。
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觉得活着比死,更艰难。
有网友在微博上向他倾诉得了抑郁症,他没劝世界多美好之类的话,只回应一个流泪的表情。他想,网友会明白他是懂得的。
他告诉记者:“没有感同身受的东西,永远没办法对等交流。”
患病之前,他也瞧不上自杀者,也会嘲笑他们。可患病之后,“得了抑郁症,想自杀,是一种疾病,并不是意志力多强就能自控。但别人不知道这种病的痛苦,哪怕是家人。我现在才治疗不到一年,但有患者朋友已经治了四五年。旷日持久了,朋友不再会安慰,甚至可能奚落你。就连家人,也可能会烦你”。
这是采访中,时常爽朗大笑的他,唯一一次情绪激动。
他说,作为一名抑郁症患者,他要打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己与自己的战争。
出口
这位老兵打响的第一仗,是将76小时的生死体验,以原原本本的方式付诸文字。
近5万字见血见肉的珍贵记忆,于2008年5月底动笔,历时一个半月艰难完成。书名为《幸存者》。
这艰难,并不指,左手麻木的他,只能用右手的一个手指敲字;而是指,一个半月的反复回想,就像重新经历濒死伤痛,耗尽心力。
但这本书写完之后,他的确不再那么频繁地做灾难噩梦了。那种噩梦,从他获救后的第一个晚上,就每夜每夜地折磨他。
出口,他急迫地需要出口,寻找出口。
《幸存者》出版后,获得了媒体颁发的散文家奖。这是1966年出生的他,此前从未得过的奖。
许多读者来信,表述感动,也鼓励他好好活下去。这样的温暖,让他在一次次与噩梦斗争时获得力量。在给读者回信中,他写道,哪怕世界上还剩下一位读者,我也会继续写下去,而且要写更多温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
于是,他又写了长篇小说《救赎》。这是汶川地震中痛失独子的一对夫妇的故事。幸存者何国典跟随在洗脚店打工的妻子来到上海,在善良人们的关怀下,一步步走出灾难阴影,走向自我救赎之路。
出乎记者意料,这个虚构的故事,却有着无比真实的生活原型。李西闽说,他确实是在一家洗脚店遇到了书中的妻子原型,也确实听她忆起了地震中丧生的独子。只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这位妻子,总在埋怨丈夫没保护好儿子,而不似书中那般坚强明亮。
她居然愿意和陌生人谈这么悲痛的事?记者问。
对,而且我鼓励受灾者把难过统统说出来,哭出来。他答。
今年4月21日,雅安地震的第二天,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建议:“在灾区,碰到那些悲伤的幸存者,不要让他们不哭,让他们大声哭出来,内心的伤需要释放。”
哭泣等释放情绪的方式,是文学之外的另一个出口。
但素来坚强的他,起初并未意识到。硬汉,怎么能哭?
获救后,在华西医院一条拥挤的走廊上,他见到了从上海赶来的妻子。他看着她,笑了笑;她看起来也很镇定,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看上去还不错嘛”。
之后,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全国各地的记者,蜂拥而至。半身麻木的他,一直在接受采访,说了一遍又一遍。
夜里,闭上眼睛,又干又涩的眼睛,泪水自动流出。但却依然不是在哭。
直到转院回沪的次日,妻子抱着一岁多的李小坏来看他。孩子脸上没有笑容,认真而严肃地盯了他一会儿,而后伸出小手,在他被削了一块的右膝盖上,轻轻地摸了一下,轻声叫了一声“爸爸”。这个地震前刚满周岁的孩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就是“爸爸”。
他心里一软,稍稍地哭了。
亲人,是他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他领记者参观李小坏的房间,骄傲地展示女儿正在练习一百以内加减法的小黑板。
他说,好几次,企图从35楼跳下,都是女儿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我晓得,她需要我,她不能没有爸爸。”
因此,他在竭尽全力地与死神搏斗、与病魔抗争,尽管不知道有没有胜算。
活着
他对记者说,治抑郁症的药吃了8个多月,自觉已有好转。
但有时,他就是不愿吃,偷偷逃掉两顿药,每次都被妻子敏感“逮”到。
病这么难受,为何还不吃药?记者问。
每顿都要吃十几种药,吃了就昏昏欲睡;妻子上班,女儿上学,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大半天就过去了。他答。
对于一位以写作谋生的人,这无疑是残忍的。
不再有敏捷文思,不再可能笔耕不辍,以往20万字的长篇用两个月构思、一个月写完,如今仅构思就得半年,写作速度也降至原先的1/4。
2013年,他一定要完成为女儿写本童话的心结。如今,刚动笔。预计十几万字,年内出版。
“是写李小坏的爸爸碰到许多稀奇古怪的妖怪。有趣,但也有一些黑暗的部分。”他的观点是,“不要总给小孩灌输美好观念,不要怕孩子发现原来世界有那么丑恶的一面,这样她内心才会强大,对于恶的一面才有抵御能力。”
给孩子写书,于他而言,是件很重要、也很美好的事情。在写作中,“必须倾注爱,而爱,是救赎的最好方式”。
救赎,是他博客里常见的字眼。
他说,他用不同的方式抵抗噩梦,希望获得灵魂的救赎。而获得救赎,最关键是让心灵安宁。
《幸存者》的版税是12%,他没拿一分钱放进自己口袋,而是资助了多名汶川地震后的贫困孩子。捐款之初,他告诉孩子们,不用感恩,只要好好读书就足够了。
实际上,他很反感“感恩”这个词。在这位客家人看来,“恩”暗指施舍,“感恩”则暗藏了道德绑架的意味。
“如果我还活着,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会一直做下去,不是为了名声,更不是为了回报,而是我内心的需要。”
2010年玉树地震后,他勇敢地到了灾区,为没钱过冬取暖的灾民捐款,还买了不少加厚的帐篷,并发动网友捐款。
他当然尚未消除对地震的惨痛记忆,他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那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在帮助他自己。
2011年,《幸存者》再版,版税同样一分不留,全部捐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去年9月,他自杀一事经由四川媒体报道后,受资助的那些四川孩子的老师看到了,流泪了,而后告诉了孩子们。孩子们合影了一张照片,寄给他。在他们身后的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李西闽叔叔,我们永远爱你。”
那个时刻,他哭了。
“我相信,那些孩子们心里有爱,等他们长大成人,他们也会去爱别人,帮助别人。这是我个人内心的事情,我会一直做下去。”迄今为止,他所资助的福建老家、玉树灾区、四川灾区的贫苦孩子,共达20多名,开销占他收入的30%有余。
一周前,他飞了一趟北京,为一部纪念汶川地震五周年的纪实文学作品《汶川地震168小时》首发式“站台”。在首发式上,他很认真地说: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们习惯遗忘,灾难发生时一窝蜂而上,哭天抢地,而后无声无息,但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们要反思,要准备好,才能从容应对下一场灾难。
他无法绕过黑色的“5·12”,他也认为不应绕过。
2013年,还要做些什么?他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治病。
也许,活着就是天堂。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