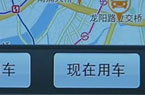顺德逢简水乡的龙舟艺人塑像

顺德逢简村金鳌桥。桥头、树下、村口,都是旧时龙舟艺人卖唱的地方(钟哲平/摄)

吴家耀挂着自制的行头在唱龙舟(钟哲平/摄)

著名艺人关心民演唱龙舟


海珠中路小学龙舟说唱团的小朋友用龙舟歌的形式唱出垃圾分类常识(钟哲平/摄)

崔同碧老师是热心义工、海珠中路小学龙舟说唱团组织者(钟哲平摄)

吴家耀做的木雕龙舟

占经楼印龙舟歌(钟哲平/摄)

清代木鱼龙舟书(钟哲平/摄)

清代和民国时期书坊出版的各种龙舟故事(钟哲平/摄)

广州群众艺术馆的吴家耀(中)把广东龙舟唱到了北京天坛
羊城晚报记者 钟哲平
自从逢简的世外风光被摄影爱好者“泄密”,这里成了游人周末踏青的好地方。在巨济古桥边,今年新添了几尊雕塑,成为水乡新景。一件雕塑是卖鸡公榄的男子,一件是买蚕茧的姑娘。另一件较为陌生,是一个男子和小孩同行,男子胸前挂小锣鼓,边走边唱。小孩左手举着一个小龙船,右手拿小钵子,似作乞讨状。雕塑底座写着“龙舟说唱”。
为了追寻木鱼、龙舟、南音、粤讴这些日渐消失的岭南绝唱,羊城晚报记者四处走访旧街老巷、乡野溪头,寻找硕果仅存的老艺人。当记者问逢简村的艄公李叔会不会唱龙舟时,艄公说:“唔识咯,我们这里有儿有女的人不会唱龙舟的,那是乞食歌。”这确是龙舟的起源。龙舟说唱在清末曾与士大夫阶层有过短暂的亲密接触,但很快被优雅的南音所取代。随着社会娱乐的丰富和文艺观念的更迭,龙舟说唱已近绝迹。如今在岭南水乡偶闻龙舟,多是旅游节目,或饭店招徕客人的表演。能够演唱完整龙舟歌的民间艺人已难觅。
春雨连绵,顺德杏坛逢简村内,河水盈润,老树蓊郁,古桥折叠。细雨湿流光的水乡风情更胜江南。
自从逢简的世外风光被摄影爱好者“泄密”,这里成了游人周末踏青的好地方。在巨济古桥边,今年新添了几尊雕塑,成为水乡新景。一件雕塑是卖鸡公榄的男子,一件是买蚕茧的姑娘。另一件较为陌生,是一个男子和小孩同行,男子胸前挂小锣鼓,边走边唱。小孩左手举着一个小龙船,右手拿小钵子,似作乞讨状。雕塑底座写着“龙舟说唱”。
此龙舟并非端午龙舟竞技,而是一种广东独有的说唱艺术。粤语说“唱龙舟”、“扒龙船”,是有区别的。今人大多只知“扒龙船”,不识“唱龙舟”了。
为了追寻木鱼、龙舟、南音、粤讴这些日渐消失的岭南绝唱,羊城晚报记者四处走访旧街老巷、乡野溪头,寻找硕果仅存的老艺人。当记者问逢简村的艄公李叔会不会唱龙舟时,艄公说:“唔识咯,我们这里有儿有女的人不会唱龙舟的,那是乞食歌。”这确是龙舟的起源。龙舟说唱在清末曾与士大夫阶层有过短暂的亲密接触,但很快被优雅的南音所取代。随着社会娱乐的丰富和文艺观念的更迭,龙舟说唱已近绝迹。如今在岭南水乡偶闻龙舟,多是旅游节目,或饭店招徕客人的表演。能够演唱完整龙舟歌的民间艺人已难觅。
壹
老街里的童声说唱
令记者惊喜的是,除了逢简村的龙舟雕塑,在广州老城区,竟然还有活着的龙舟说唱。
今年元旦过后,广州诗书街温良里社区的一片工地正在施工,街道狭窄的小路就更窄了。小路中有几排凳子,小区的公公婆婆在这里等待他们的老朋友。海珠中路小学龙舟说唱团的辅导员崔大纶与崔同碧老师带着孩子们来了,孩子们举着废旧纸皮做的龙舟模型,唱起崔大纶写的《垃圾分类齐参与》。工地传来轰隆声,稚嫩的歌声被覆盖了。社工跑到工地,请他们暂停一下。在窄长的半条老街里,在施工的间隙中,孩子们唱起了清脆的龙舟歌。
“垃圾分四类,大家要听清。养成好习惯,人人话你醒。建设新羊城,处处好干净。美景现眼前,幸福又安宁。”孩子唱得兴高采烈,节奏感很强。负责敲锣鼓的甘展豪同学说:“唱龙舟好爽,就算心情唔好,一唱就好舒服了。”甘展豪是六年级二班的学生。他敲锣鼓很落力,唱得神采飞扬。他和说唱团的其他小同学一样,是被这种游戏一样的歌谣吸引,作为校园兴趣班报名学龙舟的。他们经常在学校和社区表演,演唱的内容也常新。新时期广东精神、广州创文、申办亚运、尊师重教、孝顺父母等题材,都是他们的歌词。崔大纶编写的龙舟与时俱进,实用性很强。
诗书街街道工作人员说,让小学生唱龙舟来宣传社区文化,比张贴文件好多了。社区里的老人喜欢小孩子,孩子们也得到展现才艺的舞台。这种新颖的社区活动一举多得。
贰
古老的“新颖”
其实这种“新颖”的说唱游戏,在广东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是古老的玩意了。
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了几种粤调说唱文学的雏形。木鱼、龙舟、南音、粤讴等几种说唱艺术有递进演变的过程,也有区别并存的关系。“其歌之长调者,竟日始毕,令人感泣前襟”,即木鱼。“其短调踏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即龙舟。
木鱼是弹词的一种,产生于晚明,多为长篇故事。歌者摘出精彩部分组成情节紧凑的版本,称为“摘锦”。清代乾隆年间,受北方子弟书影响,广东出版木鱼书的书坊开始刊印短篇故事,易于携带和传诵,大大加速了说唱艺术在岭南的传播。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东一口通商,繁华的商埠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激增。开口就唱、伴奏简单的龙舟说唱,就如珠江水一样流遍富饶的珠三角地区。
话说当时顺德龙江有一破落公子阿德,不事农耕,卖唱度日。他觉得木鱼书太长,很难“揾食”。就自制一副小锣鼓挂在胸前,手提木雕龙舟作为标志,沿街卖唱。这种新鲜的说唱方式自成节拍,清脆明快,大受欢迎,被称为“短调木鱼”,亦称龙舟。阿德自此被称为“龙舟德”。龙舟说唱引来众多“斯文乞儿”效仿,纷纷举着木雕龙舟卖唱,多是唱些吉利话,如“龙舟到门前,添福又添寿”、“出入平安万事胜,东成西就百业兴”。闻者欢喜,便打赏衣食财物。
“龙舟德”的传说,比起天地会创龙舟的说法更可信些。据传天地会转向珠江水网活动时,曾流传过一首龙舟歌:“天生朱洪立为尊,地结桃园四海同。会齐洪家兵百万,反离挞子伴真龙。清连举起迎兄弟,复国团圆处处齐。大家来庆唐虞世。明日当头正是洪。”这首歌每句的首字,连起来是“天地会反清复大明”。有人说龙舟艺人胸前的一锣一鼓,代表日和月,合起来就是“明”字。这种说法富于想象力,但未免牵强。当龙舟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时,天地会确有可能利用龙舟来传播反清思想,甚至起到联络作用,但并不能认定龙舟起源于此。
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都属于单因起源说,不可尽信,但至少说明龙舟说唱到了清代,已在广东巷陌皆闻。
叁
但求两餐温饱,何计四处漂流
进入民国,龙舟就更盛行了。说唱艺人除了到人家门前唱祝颂词,也在码头、祠堂、村头等公众场合演唱,内容也从吉利话演变为讲故事。一曲唱罢,说唱者解下铜锣作盘,走向围观人群,大家便随意打赏。乡间最常见的是贺岁龙舟,如“老爷本事好名声,奶奶乐善好施心地正,少奶有喜又添丁,细蚊仔快高长大兼生性……买下良田有万顷,收租收到去五羊城。龙舟唱过人人高兴,大把利是派俾我拎。”龙舟艺人就算衣着“烂身烂世”,手中龙舟也定要精美风光,这是一种传统。龙舟长约三十厘米,四周挂红布裙,船头船尾精雕细琢,船内有小木偶,船桨与船底铁环相连。拉动铁环,木偶就整齐划桨,栩栩如生。龙舟举起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船头向外,木桨就扒水向内,以水为财。船头调转,则非常忌讳。故有龙舟艺人到门前,店铺老板都会打赏。
前文提到的海珠中路小学龙舟说唱团辅导员崔大纶的龙舟师傅,是广州群众艺术馆的退休馆员吴家耀。吴家耀编写了一首龙舟歌,生动地唱出了旧时龙舟艺人的生存状态——“锣鼓响啊,唱龙舟啊舟。呢种广东嘅歌谣体,已经有百载源流。过去嘅民间艺人,都系靠卖唱糊口,手拎住呢只锣鼓,拎住个只龙舟啊舟。或在江中渡船,或在沿街行走,但求两餐温饱,何计四处漂流。唱下水浒三国,又唱下西游记个只马骝。如果行到大户人家,就更加要讲究了喔,龙头龙尾添福啊寿,老少平安就到白头,以前嘅龙舟艺人,就系咁唱嘅啦。”
当龙舟超越祝颂乞讨,成为民间戏曲表演,曲目也丰富起来。龙舟唱本有五大内容。一是将现成的木鱼改编成精简的龙舟,如《碧容探监》、《背解红罗》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二是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的精彩情节提炼成龙舟;三是将著名的戏曲改编成浅白易懂的龙舟,如《西厢记》、《长生殿》等;四是社会时闻,如《火烧大沙头》、《辛亥广东米贵兼闰月》、《三元里抗英》等,龙舟成了农村民众的资讯来源;五是以民间传说和警世故事来劝善,内容多为仁义孝顺、因果报应。有一首《孝顺歌》,朴实感人——“一闻你哭就快把儿抱,忘餐废寝不惮勤劳。好物口悭留番个仔肚,教行教话左右拖扶……不料娶妻之后又到你地公婆好咯,又话老野不合潮流我地自己煲……一旦双亲死后好似身离苦,灵前痛哭把尘铺。唉,酒席焉能入得鬼肚,你地在生唔敬奉死后何劳。”上世纪80年代,香港著名古腔粤曲唱家李锐祖在茶楼演唱这首龙舟,字字清景,拖出淡淡凄凉,但没有一点怨气,只是唱出一种“老窦养仔仔养仔”的人之常情,令人在隐隐的愧疚中感念亲恩。
曲目丰富后的龙舟故事引人入胜,茶楼食肆纷纷请龙舟艺人表演以吸引食客。清末民初有不少瞽师,如“龙舟珠”、“龙舟松”、“龙舟锦”等,都是茶楼的抢手唱家。据香港著名瞽师杜焕回忆,他上世纪20年代到香港,就和同行“盲华”在茶楼唱龙舟。长篇龙舟比精炼的南音更耗气,瞽师全凭记忆唱得绘声绘色,殊为不易。杜焕在香港富隆茶楼录制的南音唱片中,有这样一段开场白——“今日又试向各位拿个人情,吵嘈下各位贵客嘅发财耳,往日唱南音,今日就唱龙舟。祝各位横财顺利,一帆风顺,东成西就。老者听过就添福添寿,后生听过就出人头。”据杜焕的学生、民族音乐学博士唐健垣介绍,杜焕不善高谈,往往唱多说少。他唱龙舟时一改风格,说一大段才开唱,正是体现了“吉利龙舟”的特色。
曲目的丰富令龙舟的伴奏形式也丰富起来,龙舟开始被粤曲吸收,产生了有别于街头龙舟的舞台龙舟。舞台龙舟不用锣鼓,多为清唱,令观众更聚精会神。舞台龙舟在听觉上“清清白白”,可和多种板腔与小曲连接,灵活生动。
舞台龙舟的出现,使龙舟摆脱沿街乞食的印象,始登大雅之堂。龙舟艺人的身份也有所提高,一些稍通文墨的艺人编写的唱词,文采斐然,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上世纪20年代,佛山有位艺人何二珠,又名“龙舟珠”,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略通诗词,唱起龙舟来徐疾有致、入情入理,感染力很强。佛山很多大户人家都争相请“龙舟珠”到喜宴上表演,每每蓬荜生辉。“龙舟珠”的生意好到要预约排期。据闻骆秉章、张荫桓、戴鸿慈等清末粤籍大吏的后人,都请过“龙舟珠”到府上演唱。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提到,叶问夫人张永成喜欢听曲,常去听南音。这位张永成是张荫桓的侄女,她听曲的兴趣,是不是从小在家中听“龙舟珠”培养起来的呢?这纯属臆想。但“龙舟珠”到张府唱曲的掌故,反映了龙舟说唱已从底层社会进入官宦世家,被士大夫阶层所欣赏。
肆
龙舟歌中的实用主义
龙舟受欢迎,渐渐成为一种宣传工具,说唱内容也与时俱进,紧跟形势。
民国时期,龙舟在劝人戒烟戒赌、宣传男女平等、破除封建迷信方面,都有不少传唱一时的作品。旧时广州市民有在城隍诞前夜到城隍庙“打地气”的习俗,通宵在庙堂睡地铺,祈求神仙上身,消灾除病。龙舟《打地气》就讽刺了这种旧习——“真正好笑,嗰啲打地气嘅痴人,做乜肯作践自家身?咁好高床暖枕你都唔瞓,迷头迷脑好似失咗三魂。你睇辘在庙堂天咁笨,半夜三更走去喂蚊。未必拜过城隍就会行好运,咁就世间人仔使乜忧贫。”
龙舟的“功用”在解放初至“文革”后期发挥到极致,一度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轻骑兵”。如《韩大哥捉特务》、《军属模范刘大娘》、《书记让车》等,就是当时劳动人民流行的龙舟。这批“实用”的红色龙舟,歌词拗口,韵律牵强,但却是特殊时期文化氛围的真实反映。歌颂小英雄的有:“冬子把红星镶在军帽上,只见光芒照四方。冬子下定决心,永远跟着党,看今日新芽壮,明天好栋梁!”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有:“毛主席生前,多次把警钟敲响,要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佢地钻入狗洞开黑会,好似被追捕嘅豺狼。”
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提高,龙舟就开始唱《菜篮歌》。以往市场是“每日上市菜蔬只得三五担,品种少时又简单。清一色来点到你挑挑拣拣,又黄又老令你睇到就心烦”。开放后的餐桌是“老公想食萝卜煲牛腩,大仔要试塘蒿滚鱼生,二女叫买韭黄炒滑蛋,细仔嘈住腊肉烩芥兰”。一日三餐有好菜,一家人开开心心食饭,就是老广对好日子最朴素的表达。
伍
静思往事,影像流传
时移世易,知道龙舟的人越来越少了。据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还有龙舟艺人在老城区走街说唱。顺德龙舟艺人何志宁还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唱龙舟。这些老艺人渐渐年迈,他们的歌声如风烛飘摇。广州如今已少横街窄巷,更不闻龙舟说唱。但在中山、顺德、东莞等地的村落,仍有木鱼、龙舟的余音。据中山的粤曲爱好者介绍,几年前逢年过节还有龙舟艺人戴上整副行头卖唱,有人会请他们回家“赠庆”。清明时节,也有说唱艺人到人家拜山的山头,问要不要唱几句龙舟诉诉衷情。如今只在某些官方举办的“艺术节”上偶见龙舟客串,唱词多为歌功颂德,已难觅昔日淳朴的生活气息。
虽然有所变调,但龙舟说唱的适应性与实用性,又令它的生命得以顽强延续,比后于它产生的南音与粤讴更加“长命”。
前文所说的广州海珠中路小学龙舟说唱团,就是龙舟存活的证明。海珠中路小学李校长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说唱团是退休教师崔同碧组织起来的,为学生提供了展现才华与回报社会的平台,能与学校德育工作中的感恩教育结合,对传承广府文化也有一定作用。令李校长意外的是,报名参加龙舟说唱团的,并不全是广州仔,还有不少外来工子弟,有些连广州话都讲不正。他们报名的原因是,其他声乐、舞蹈、航模等兴趣班的学费与配套消费太高了,而龙舟说唱的门槛最低。
说唱团的辅导员崔大纶、崔同碧姐弟是广州著名义工。崔大纶是广州荔湾区青少年宫的退休教师,辅导过200多位智障儿童。崔大纶姐弟用废旧的材料做成“环保龙舟”,让孩子们拿在手中表演,竟让古老的龙舟有了卡通的趣味。童声稚嫩,情态殷殷,“社区龙舟”脱胎而生,为古老的艺术注入鲜嫩的朝气。崔大纶说:“人一世做不了多少件好事,做得一件是一件。”
崔大纶的龙舟师傅吴家耀的观念,则更为简单。他说:“民间艺术没什么专家、专利可言,越多人知道越好。我们谈不上挽救什么,不过是上了年龄的人,讲多些我们知道的事情,给不知道的人听。”
吴家耀曾专程到顺德寻访龙舟艺人,模仿他们的木雕龙舟,亲手做了一套精致的龙舟行头。2004年,吴家耀带着自制的龙舟,把广东龙舟唱到了北京天坛。鸡公榄、吹嘀嗒(唢呐)、龙舟歌等岭南民间艺术,连不懂粤语的老北京也听得津津有味。
吴家耀退休前曾在广州市二文化宫与著名民间老艺人关心民搭档讲相声、唱龙舟。关心民退休后,一直对龙舟念念不忘。他生命最后的几年,每天都搬张凳仔,在洲头咀码头附近的街道坐上大半日。关老西装革履,默默地望着路人来去匆匆。有人和他打个招呼,他就点头微笑。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每天在街头看落日,成为广州一景。千禧年前夕,广州文献学者梁基永去拜访关心民,常常站在大街上跟关老师学唱南音。学了几天,关心民对梁基永说:“不如你先学龙舟吧,龙舟更偏门,更少人唱了。”于是关心民就教梁基永唱龙舟,一曲未教完,先生就离世了。关心民生前送了一张照片给梁基永,照片背面题着一首小诗——“几回静坐思往事,影像流传见当时。”
钟哲平
(来源:羊城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