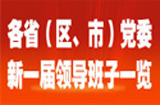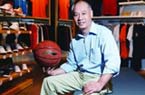工作时的吴永亮。
本报记者 王烜
【人物简介】
吴永亮,1937年生,扬州人。上海湘铭理发店学徒出身,北京四联美发建店元老。北京市美发业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上世纪50年代,为支援首都建设,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从上海挑选“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名店,于1956年迁至北京,坐落在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33号,7月27日正式开张营业。“四联”迁京,引进了先进的理发设备和技艺,把南方的细腻、时尚与北方的朴实、庄重融为一炉,很快受到首都各界人士的欢迎,享有极高声誉。吴永亮从那时起,长期在一线工作至今。
内联升的鞋,盛锡福的帽,瑞蚨祥的绸缎,同仁堂的药……声震京津的一家家老字号,分列在熙攘的王府井大街,鳞次栉比,交相辉映。生年不满甲子的“四联美发”,侧身百年老店之间,略显含蓄与婉约。正门是一张女士秀美的脸庞,加之一头飘逸的长发,背景以红、白、蓝、黑四条波浪,展示人们追求美、崇尚美的境界。进入店堂,一群忙碌的女理发师。二楼的名人屋内,坐满了等候的宾客,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师傅边和顾客唠着家常,边熟稔地操练手中的滚刷和吹风机,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吴永亮。
75岁的吴师傅如今每周来上两天班,他和四联或许谁也离不开谁。听闻记者来采访吴永亮,正在做头的女士紧忙开了腔:“要写吴师傅,这可太好了,这样的人应该多宣传。我跟吴师傅这30多年了,这屋里全是他的老主顾。”
送走了客人,已近下午5点。“从早晨8点到现在没闲着,让您久等了。”记者好奇“四联”早上开业时间如此之早,吴永亮解释,“9点开门,但都是老朋友,人家8点有空我必须得来。”吴师傅听说是上海的媒体,显得很兴奋,“我一个手艺人,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上海父老能想到我这个小人物,很感谢!我的故事也要从1950年的上海讲起。”
小小少年的海上梦
吴永亮是老扬州,兄弟5人,他排行最小。扬州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服务业异常发达,“三把刀”驰名四海。吴永亮学理发,和家乡的土壤密不可分。“也是没文化,够档次的工作干不来,只能耍手艺。”吴师傅说起自己的从业缘由倒是干脆。
湘铭理发店坐落在愚园路,毗邻百乐门,吴永亮的姑父是这家店的老板,姑父辞尘后,姑母接管经营。他的两个哥哥都到这儿当学徒,老家的地有父兄照顾,13岁的吴永亮被家里决定送往上海,“那时刚解放,学徒的规矩还是没变,经保人推荐,立了契约,我就和同伴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或许上苍有意考验这位到上海寻梦的少年,在火车站吴永亮和领路人走散了。他和另一位同乡都不识字,就拿着地址一路打探走到了湘铭店前。时已子夜,两个小伙伴不敢敲门,在街头露宿了一夜。次日天明,旁边的豆腐坊开门,经询问确认是湘铭理发店,他们才得以进入。大上海的一切都令13岁的吴永亮惊诧不已:“农村那时连电都没有,上海霓虹灯闪烁,我是头一次看见电灯。我下定决心,要在这块土地生存下去。”
所谓学徒,师傅是不会主动教授技艺的,徒弟实际就是义务杂役。洗毛巾、擦地、倒马桶,店里的杂活吴永亮全都干过,阴冷的洋灰地就是他的床铺,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半。吴师傅说,能不能学到手艺就看自己用不用心,干完了杂事就在旁边看师傅做活,跟师兄主动求教,自己私下练。记者打听传说中的“剃冬瓜”,吴永亮笑笑:“老师傅有这种说法,但我们没用过,都是拿自己的腿练。膝盖部位就是练习的靶子,拿刀上下刮,练腕子功,那会儿腿上净是刀伤,功夫就这样练出来的。”三年师满,吴永亮依然没有实践的可能。“我那时心里着急,想早点做活好赚钱,就跑到棚户区为人义务理发。”手艺逐渐提高后,吴永亮终于盼到在店里拿推子的机会了。
1956年,湘铭理发店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完成了转制,成为国家工人的吴永亮心里平添了底气,他觉得自己有了在上海落脚生根的本钱。只是他未曾想到,仅仅一周之后,命运之手将他推向了遥远的北方。
一百单八将进京城
“那天下午,工会组长召集大家开会,宣布湘铭等四家店迁京。北京方面承诺,上海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家属一年之内全部调入北京。”吴永亮对当日情形,记忆深刻。他说,大家对党的号召没有二话,而且上海理发业竞争太激烈了,我们也想:换个地方或许好干。时年19岁的吴永亮是迁京人员里最年轻的,没有家庭负担,他得以轻装上路。四家理发名店总共108人,一锅端到了北京,他们戏称是“一百单八将进京城”。
经过36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上海师傅到了首都。北京一商局在鲜鱼口为大家接风洗尘,众人流连于前门一带的繁华,心里憧憬着北京生活的美好,可到了住地却大跌眼镜。“我们被安排在工体住宿,那时就是一片荒地,跟农村差不多,我当时心里挺有落差的,觉得北京比上海土气。”吴永亮说。
随后的半月里,北京方面安排上海师傅览故宫、游北海、访颐和园,把京城名胜看了十之七八。休息整顿之后,下面就要研究如何在北京落脚了。1955年,北京西单第一理发馆已引进了上海师傅,但这些北迁的匠人出现了水土不服。吴永亮说:“我们去西单第一理发馆学习考察,那里的上海师傅跟我们诉苦,说与北京师傅的技术理念不合,在这吃不开。”“四联”因是清一色的上海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关键是让北京人认可海派风格。
最初的打算是四家店分置四城,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听说东单理发馆那地段不错,北京方面马上下令:东单理发馆腾地儿。就这样,1956年7月27日,“四联理发馆”在王府井大街北口金鱼胡同33号正式挂牌营业。“四联理发馆”五个字之下还有一行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
机缘巧合,记者采访当日,遇到了一位“四联”的铁杆粉丝。孙女士是位地道的老上海,1955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爱美的她始终为找不到称心的美发师发愁。“四联”开张的消息一传开,孙医生就兴奋不已:“家乡师傅的手艺就是好,开业第一天我就来了,也是那一天认识了老吴,我们俩同岁,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了。”吴永亮在一旁打趣:“孙医生每星期来一次,风雨无阻,她的爱好就是烫头。”
北京人的发型如同这座城市,深厚、庄严,然而缺少灵动、飘逸。当时北京的女士烫发只有大花、小花的样子,过于呆板。上海是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地方,发型也遥遥领先北方。时尚新颖的样式,加上优质的服务,“四联”很快在京城叫响,为北京美发行业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吴师傅介绍,上海师傅的吹风技术可以作为表演节目,他本人就是凭借同时操作5把滚刷赚取了名声。
“四联”有一句话:宁把客人等走了,也不能把客人做跑了。北方人习惯称呼“您”以示尊重,可南方没有这个音,为了融入北京,上海师傅苦练语言,最终人人过关。“您字开头,请字张口”,也成了“四联”的店规。这里服务的精致,可从毛巾看出。在“四联”,一位男宾剪头、刮脸共需要8条毛巾。进门擦脸1条,洗头2条,刮脸5条。女宾的用具全部是酒精消毒,墙上张贴消毒标准,向顾客公示,以示童叟无欺。在东华门建立了专门的消毒车间,每天都有一辆三轮车往返于王府井大街和东华门之间,专为运送毛巾。
诚然,“四联”的收费也是京城的头牌。上世纪50年代,北京剪发都是4毛钱,“四联”却是8毛钱,烫发2.2元。即使如此,照样宾客盈门。收入低的市民,平时舍不得,过年前也要咬牙进“四联”享受一回。吴永亮说,那几年每到腊月就睡不了囫囵觉,他最忙的时候一天剪发130个,烫发40多个,月收入破百元,在当时绝对是高薪。
名声大噪,来“四联”求职学徒的人也多了,这时又一幕让上海师傅感到不适应。“北京女孩子也学理发,这是上海不可能的,老师傅都说祖宗没留这规矩。”老吴也弄不清北京女理发师是从何时产生的,当时经过组织上做工作,他们才尝试带女徒弟。也许轮回就是如此吊诡,如今的美发行业又是男人的天下,只有这国营的“四联”依稀可见女师傅身影,反而成了北京的一景。
1960年以后,吴永亮已是店里的名师了,手艺好、人品好、形象好,是顾客对他一致的评价。中央部长、驻华使节、文化名流,都成了老吴的主顾和朋友。技术上出了头,在北京成了家,进京的第一个十年,吴永亮过得挺惬意,直到那年的春雷乍响。
发型折射时代变迁
“到北京第二个十年,是我最郁闷的十年,我当时认为这辈子也拿不起吹风机了。”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四联”,用大字报将镜子全部给糊上,然后勒令“四联”不许烫发。“大街上穿高跟鞋的,红卫兵上去就把鞋跟儿敲掉,就更甭说发型了。不仅不许烫发,连卷发、包头都不成,甚至要求头发不许过肩。”吴永亮低沉着说。“四联”女部就此取消,老吴只好转到男部去理发。“四联理发馆”的名字,也被符合当时时代特色的“新风理发馆”所代替。
“美发师的手艺,可以说是为女性专设。不能做女活了,这干着还有什么劲?”吴永亮除了本事无法施展,还着实害怕过一段。因为之前的很多顾客,一夜间成了“牛鬼蛇神”,为他们服务的吴永亮担心自己难逃一劫。“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福芝芳,我被迫得罪了她。”
“四联”开业之初,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就来光临,年轻有为的吴永亮是她最信任的师傅。梅兰芳辞世后,孀居的福芝芳不想出门,就请吴永亮上门服务。“梅家祖籍泰州,和我算同乡,梅家人跟我关系处得挺好,老太太很喜欢我。可是后来局势变了。”当时,店里有小字辈说吴永亮专为“反动权威”服务,老吴害怕挨整,福芝芳再打电话,他百般推脱。这位梅夫人也是戏班出身,虽然年纪大了,但江湖血性尚存。一日,竟亲自找上门来。“那会儿北京只有一辆私家车,就是梅先生的奔驰,谁都认识。老太太的车一来,就有人告诉我了,我赶紧躲到后面,这下她真生气了,到死不登门。”吴永亮说起这段往事,言语中透着愧疚。梅葆玖也是吴永亮的固定客人,一次他来剪头,吴永亮低声说:“我是没办法,劝劝你母亲,别生气。”已然落魄的梅葆玖心领神会:“谢谢吴师傅,您也多保重!”“哎,那个情况,还能说什么?”老吴一声长叹。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吴永亮被调到那里工作,在战战兢兢中步入中年。1976年底,吴永亮被调回“四联”,领导悄悄告诉他:准备做女活。“我当时不敢相信,心早死了。再说十年没烫过发,还干得了吗?”文革虽然结束,但禁忌尚在,吴永亮不敢承应。领导透露说,文艺界现在要对外交流,总得讲个形象,凭单位介绍信可以烫发,但不许做波浪,只能烫点花再扎起来。就是这小小的一个口子,让老吴又忙得不亦乐乎。“我第一个接待的是电影演员田华,她要去日本出访,结果一张介绍信,她带来4个人。”为了能烫发,文艺界当时兴起了“走后门”,三亲六故只要有在文艺院团的,都想办法来美上一回。“政治高压也阻挡不住人们追求美的权利。”吴永亮这句话颇有哲理。
改革春风吹绿神州之际,吴永亮才得以重焕生机。1978年9月底,文革产物“新风理发馆”宣告终结,修葺一新的“四联理发馆”重张营业。扩建后的“四联”,理发座椅从27把增到56把,增添修眉、纹脸、化妆和制作假发等项目,美容概念也开始登上了“四联”的舞台,最扎眼的当属四台电烫机。开业那天,有家国外电视台的驻京记者从此路过,瞅着人这么挤,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凑过来一看,原来是排队理发。这个记者看见排队等着烫发的队伍,眼睛都亮了。回去扛着摄像机就来了,上上下下一通拍。没过多久,又来一拨,一天之内来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后来,师傅们才知道,敢情人家发现了新闻点:中国许可烫发了!
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吴永亮感到了压力。“人们审美的要求提高很快,新发型层出不穷,自己又得二次学徒。”老吴喜欢看电影,不过他不只是为了娱乐,这里有他的事业。“电影里的发型就是我学习的源泉,几秒钟把构造记住,回来自己再研发。”吴永亮说,美发是技术、艺术和心理的重合,观念必须与时俱进。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老顾客和他抱怨,自己女儿在国外读书,放假回来留了个“鬼头”,母女吵得不可开交。老吴听了安慰说,“您别着急,把孩子带来我看看。”这位女士领着女儿来了,老吴一看女孩剪了个寸头。“小姑娘留短发也挺精神,咱们不能老脑筋,要尊重年轻人的自由。”王府井教堂前,经常有拍婚纱照的新人,吴永亮总会驻足欣赏一下新娘的发型。他说:“我还喜欢看街舞,我就琢磨跳街舞适合什么发型,虽然自己不一定能做,但还是得研究。”
美的力量难抵挡
通过自己的妙手裁剪,能为他人的生活注入一丝喜悦,那是吴永亮对自己最欣赏的一刻。宋女士是一位退休干部,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亲身经历。一次在公交车上,宋女士被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盯着看了好久,那位女士最终忍不住问她:在哪做的头?宋女士回答说:在“四联”。对方马上接问:是不是吴师傅做的?“您看,老吴的名气就是这么大。”几年前,河南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慕名来到“四联”,吴永亮的手艺令她印象深刻。从那以后,只要来北京,这位记者必和吴师傅预约。
吴永亮说:“追求美是不分年龄的,爱美的人不会老年痴呆。我现在只为老朋友们服务。像这位孙医生,我看着她工作、结婚、生子,又看着她孩子工作、结婚、生子,彼此都像一家人。我舍不得和老友们的这份情谊,也希望让她们一直美下去。”
四联美发的总经理吴秀敏说,吴师傅是店里的一面旗帜,他和顾客之间温暖人心的故事很多,这已是“四联”企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却定期的为老友服务,吴永亮也肩负着技艺传承的责任,如今“四联”的中青年技师,都受过吴永亮的指点。老吴也开山门正式收过徒弟,无论留下来的,还是出去自立门户的,都已经是业内颇具知名度的美发师了。吴秀敏告诉记者,“四联”能够将原有的风格一脉传承下来,靠的是师徒相传的老办法。新员工进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从基本功练起。基本功练得差不多了,年轻员工会被指派跟着一位师傅练,直到能接活为止。就拿用滚刷吹头发这个手艺来说,看似简单,想要掌握没有两三年是做不来的。“技术不成在这甭想上手。”
吴永亮有两位孩子,一位早已移居海外,他和老伴目前还住在6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房子是单位分的,离店近,上班方便,老两口也够住的。”记者问吴师傅准备干到什么时候?他说:“只要还干得动,就会坚持下去。不过毕竟这把年纪了,我知道和大家说再见的日子不远了!”
把时光倒流回62年前的上海,敲开湘铭理发店大门的一瞬,吴永亮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未知。回首前尘,他庆幸从事了这份职业,觉得自己比师辈都要幸运。“干这行的以前社会地位很低,顾客不会跟你交朋友,是新社会改变了这种风气。创造美是极其神圣的,这份职业让我收获了成就感!”
视觉设计朱伟 赵亮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